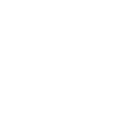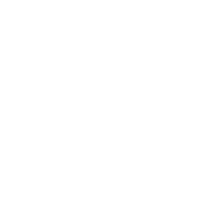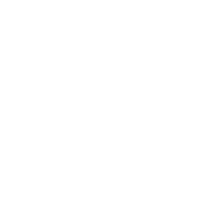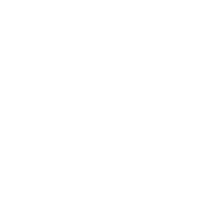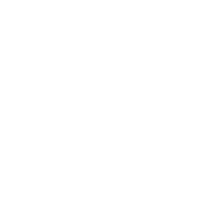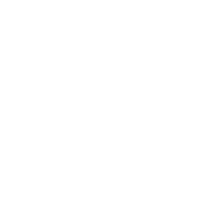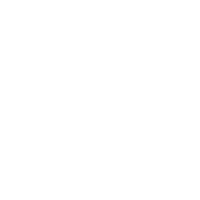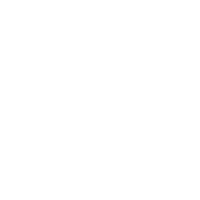庙的回忆(2),史铁生
有人说下雨也不怕,就怕一下雨家里人该着急了。
有人说一下雨蛇先出来,然后指不定还有什么呢。
那个想撒尿的开始发抖,说不光想撒尿这会儿又想屙屎,可惜没带纸。
这样,大家渐渐都有了便意,说憋屎憋尿是要生病的,有个人老是憋屎憋尿后来就变成了罗锅儿。
大家惊诧道:是吗?
那就不如都回家上厕所吧。
可是第二天,那个最先要上厕所的成了唯一要上厕所的,大家都埋怨他,说要不是他我们还会在那儿待很久,说不定就能捉到蛇,甚至可能看看鬼。
有一天,那庙院里忽然出现了很多暗红色的粉末,一堆堆像小山似的,不知道是什么,也想不通到底何用。
那粉末又干又轻,一脚踩上去噗的一声到处飞扬,而且从此鞋就变成暗红色再也别想洗干净。
又过了几天,庙里来了一些人,整天在那暗红色的粉末里折腾,于是一个个都变成暗红色不说,庙墙和台阶也都变成暗红色,荒草和老树也都变成暗红色,那粉末随风而走或顺水而流,不久,半条胡同都变成了暗红色。
随后,庙门前挂出了一块招牌:有色金属加工厂。
从此游戏的地方没有了,蛇和鬼不知迁徙何方,荒草被锄净,老树被伐倒,只剩下一团暗红色漫天漫地逐日壮大。
再后来,庙堂也拆了,庙墙也拆了,盖起了一座轰轰烈烈的大厂房。
那条胡同也改了名字,以后出生的人会以为那儿从来就没有过庙。
我的小学,校园本也是一座庙,准确说是一座大庙的一部分。
大庙叫柏林寺,里面有很多合抱粗的柏树。
有风的时候,老柏树浓密而深沉的响声一浪一浪,传遍校园,传进教室,使吵闹的孩子也不由得安静下来,使琅琅的读书声时而飞扬时而沉落,使得上课和下课的铃声飘忽而悠扬。
摇铃的老头,据说曾经就是这庙中的和尚,庙既改做学校,他便还俗做了这儿的看门人,看门兼而摇铃。
老头极和蔼,随你怎样摸他的红鼻头和光脑袋他都不恼,看见你不快活他甚至会低下头来给你,说:想摸摸吗?
孩子们都愿意到传达室去玩,挤在他的床上,挤得密不透风,没大没小地跟他说笑。
上课或下课的时间到了,他摇起铜铃,不紧不慢地在所有的窗廊下走过,目不旁顾,一路都不改变姿势。
叮当叮当——叮当叮当——铃声在风中飘摇,在校园里回荡,在阳光里漫散开去,在所有孩子的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
那铃声,上课时摇得紧张,下课时摇得舒畅,但无论紧张还是舒畅都比后来的电铃有味道,浪漫,多情,仿佛知道你的惧怕和盼望。
但有一天那铃声忽然消失,摇铃的老人也不见了,听说是回他的农村老家去了。
为什么呢?
据说是因为他仍在悄悄地烧香念佛,而一个崭新的时代应该是无神论的时代。
孩子们再走进校门时,看见那铜铃还在窗前,但物是人非,传达室里端坐着一名严厉的老太太,老太太可不让孩子们在她的办公重地胡闹。
上课和下课,老太太只在按钮上轻轻一点,电铃于是“哇——哇——”地叫,不分青红皂白,把整个校园都吓得要昏过去。
在那近乎残酷的声音里,孩子们懂得了怀念:以往的铃声,它到哪儿去了?
唯有一点是确定的,它随着记忆走进了未来。
在它飘逝多年之后,在梦中,我常常又听见它,听见它的飘忽与悠扬,看见那摇铃老人沉着的步伐,在他一无改变的面容中惊醒。
那铃声中是否早已埋藏下未来,早已知道了以后的事情呢?
多年以后,我二十一岁,插队回来,找不到工作,等了很久还是找不到,就进了一个街道生产组。
我在另外的文章里写过,几间老屋尘灰满面,我在那儿一干七年,在仿古的家具上画些花鸟鱼虫、山水人物,每月所得可以糊口。
那生产组就在柏林寺的南墙外。
其时,柏林寺已改做北京图书馆的一处书库。
我和几个同是待业的小兄弟常常就在那面红墙下干活儿。
老屋里昏暗而且无聊,我们就到外面去,一边干活一边观望街景,看来来往往的各色人等,时间似乎就轻快了许多。
早晨,上班去的人们骑着车,车后架上夹着饭盒,一路吹着口哨,按响车铃,单那姿态就令人羡慕。
上班的人流过后,零零散散地有一些人向柏林寺的大门走来,多半提个皮包,进门时亮一亮证件,也不管守门人看不看得清楚便大步朝里面去,那气派更是让人不由得仰望了。
并非什么人都可以到那儿去借书和查阅资料的,小D说得是教授或者局级才行。
“你知道?”“废话!”
小D重感觉不重证据。
小D比我小几岁,因为小儿麻痹症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了三公分,中学一毕业就到了这个生产组
很多招工单位也是重感觉不重证据,小D其实什么都能干。
我们从早到晚坐在那面庙墙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用看表也不用看太阳便知此刻何时。
一辆串街的杂货车,“油盐酱醋花椒大料洗衣粉”一路喊过来,是上午九点。
收买废品的三轮车来时,大约十点。
磨剪子磨刀的老头总是星期三到,瞄准生产组旁边的一家小饭馆,“磨剪子来嘿——抢菜刀——”声音十分洪亮
大家都说他真是糟蹋了,干吗不去唱戏?
下午三点,必有一群幼儿园的孩子出现,一个牵定一个的衣襟,咿咿呀呀地唱着,以为不经意走进的这个人间将会多么美好,鲜艳的衣裳彩虹一样地闪烁,再彩虹一样地消失。
四五点钟,常有一辆囚车从我们面前开过,离柏林寺不远有一座著名的监狱,据说专门收容小偷。
有个叫小德子的,十七八岁没爹没妈,跟我们一起在生产组干过。
这小子能吃,有一回生产组不知惹了什么麻烦要请人吃饭,吃客们走后,折箩足足一脸盆,小德子买了一瓶啤酒,坐在火炉前稀里呼噜只用了半小时脸盆就见了底。
但是有一天小德子忽然失踪,生产组的大妈大婶们四处打听,才知那小子在外面行窃被逮住了。
以后的很多天,我们加倍地注意天黑前那辆囚车,看看里面有没有他
囚车呼啸而过,大家一齐喊“小德子!
小德子!”
小德子还有一个月工资未及领取。
那时,我仍然没头没脑地相信,最好还是要有一份正式工作,倘能进一家全民所有制单位,一生便有了倚靠。
母亲陪我一起去劳动局申请。
我记得那地方廊回路转的,庭院深深,大约曾经也是一座庙。
什么申请呀简直就像去赔礼道歉,一进门母亲先就满脸堆笑,战战兢兢,然后不管抓住一个什么人,就把她的儿子介绍一遍,保证说这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孩子其实仍可胜任很多种工作。
那些人自然是满口官腔,母亲跑了前院跑后院,从这屋被支使到那屋。
我那时年轻气盛,没那么多好听的话献给他们。
最后出来一位负责同志,有理有据地给了我们回答:“慢慢再等一等吧,全须儿全尾儿的我们这还分配不过来呢!”
此后我不再去找他们了。
再也不去。
但是母亲,直到她去世前还在一趟一趟地往那儿跑,去之前什么都不说,疲惫地回来时再向她愤怒的儿子赔不是。
我便也不再说什么,但我知道她还会去的,她会在两个星期内重新积累起足够的希望。
我在一篇名为《合欢树》的散文中写过,母亲就是在去为我找工作的路上,在一棵大树下,挖回了一棵含羞草
以为是含羞草,越长越大,其实是一棵合欢树。
大约一九七九年夏天,某一日,我们正坐在那庙墙下吃午饭,不知从哪儿忽然走来了两个缁衣落发的和尚,一老一少仿佛飘然而至。
“哟?”
大家停止吞咽,目光一齐追随他们。
他们边走边谈,眉目清朗,步履轻捷,颦笑之间好像周围的一切都变得空阔甚至是虚拟了。
或许是我们的紧张被他们发现,走过我们面前时他们特意地颔首微笑。
这一下,让我想起了久违的童年。
然后,仍然是那样,他们悄然地走远,像多年以前一样不知走到哪里去了。
“不是柏林寺要恢复了吧?”
“没听说呀?”
“不会。
那得多大动静呀咱能不知道?”
“八成是北边的净土寺,那儿的房子早就翻修呢。”
“没错儿,净土寺!”
小D说,“前天我瞧见那儿的庙门油漆一新我还说这是要干吗呢。”
大家愣愣地朝北边望。
侧耳听时,也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声音传来。
这时我才忽然想到,庙,已经消失了这么多年了。
消失了,或者封闭了,连同那可以眺望的另一种地方。
在我的印象里,就是从那一刻起,一个时代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