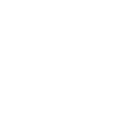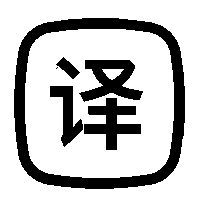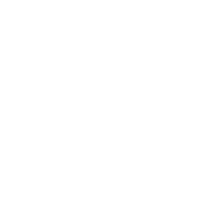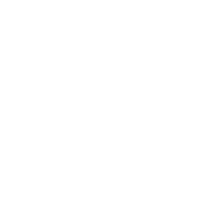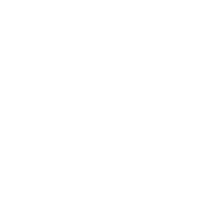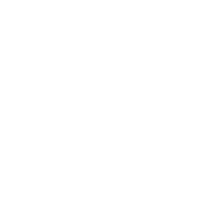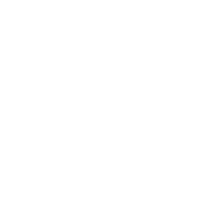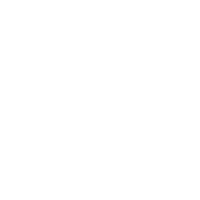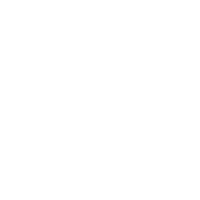寄欧阳舍人书,曾巩,宋代。
巩顿首再拜,舍人先生。
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
反复观诵,感与惭并。
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
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
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
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
此其所以与史异也。
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
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
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
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
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
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
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
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
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
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
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
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
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
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
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
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
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
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
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
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
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
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
况巩也哉?
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
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
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
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
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
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
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
既拜赐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
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
愧甚,不宣。
巩再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