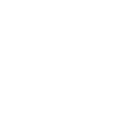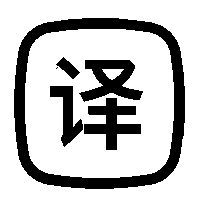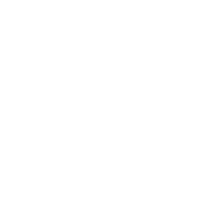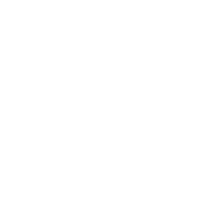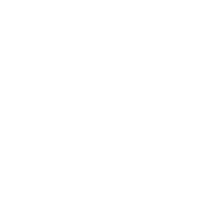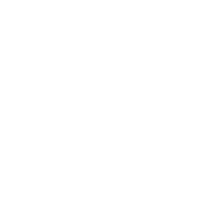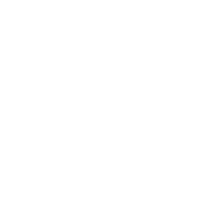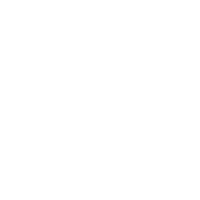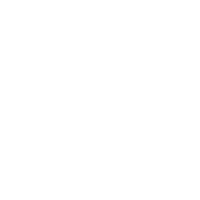茅坤《青霞先生文集序》
青霞沈君,由锦衣经历上书诋宰执,宰执深疾之。
方力构其罪,赖明天子仁圣,特薄其谴,徙之塞上。
当是时,君之直谏之名满天下。
已而,君纍然携妻子,出家塞上。
会北敌数内犯,而帅府以下,束手闭垒,以恣敌之出没,不及飞一镞以相抗。
甚且及敌之退,则割中土之战没者与野行者之馘以为功。
而父之哭其子,妻之哭其夫,兄之哭其弟者,往往而是,无所控吁。
君既上愤疆埸之日弛,而又下痛诸将士之日菅刈我人民以蒙国家也,数呜咽欷歔;,而以其所忧郁发之于诗歌文章,以泄其怀,即集中所载诸什是也。
君故以直谏为重于时,而其所著为诗歌文章,又多所讥刺,稍稍传播,上下震恐。
始出死力相煽构,而君之祸作矣。
君既没,而中朝之士虽不敢讼其事,而一时阃寄所相与谗君者,寻且坐罪罢去。
又未几,故宰执之仇君者亦报罢。
而君之故人俞君,于是裒辑其生平所著若干卷,刻而传之。
而其子襄,来请予序之首简。
茅子受读而题之曰: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遗乎哉?
孔子删《诗》,自《小弁》之怨亲,《巷伯》之刺谗而下,其间忠臣、寡妇、幽人、怼士之什,并列之为“风”,疏之为“雅”,不可胜数。
岂皆古之中声也哉?
然孔子不遽遗之者,特悯其人,矜其志。
犹曰“发乎情,止乎礼义”,“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焉耳。
予尝按次春秋以来,屈原之《骚》疑于怨,伍胥之谏疑于胁,贾谊之《疏》疑于激,叔夜之诗疑于愤,刘蕡之对疑于亢。
然推孔子删《诗》之旨而裒次之,当亦未必无录之者。
君既没,而海内之荐绅大夫,至今言及君,无不酸鼻而流涕。
呜呼!
集中所载《鸣剑》、《筹边》诸什,试令后之人读之,其足以寒贼臣之胆,而跃塞垣战士之马,而作之忾也,固矣!
他日国家采风者之使出而览观焉,其能遗之也乎?
予谨识之。
至于文词之工不工,及当古作者之旨与否,非所以论君之大者也,予故不著。
嘉靖癸亥孟春望日归安茅坤拜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