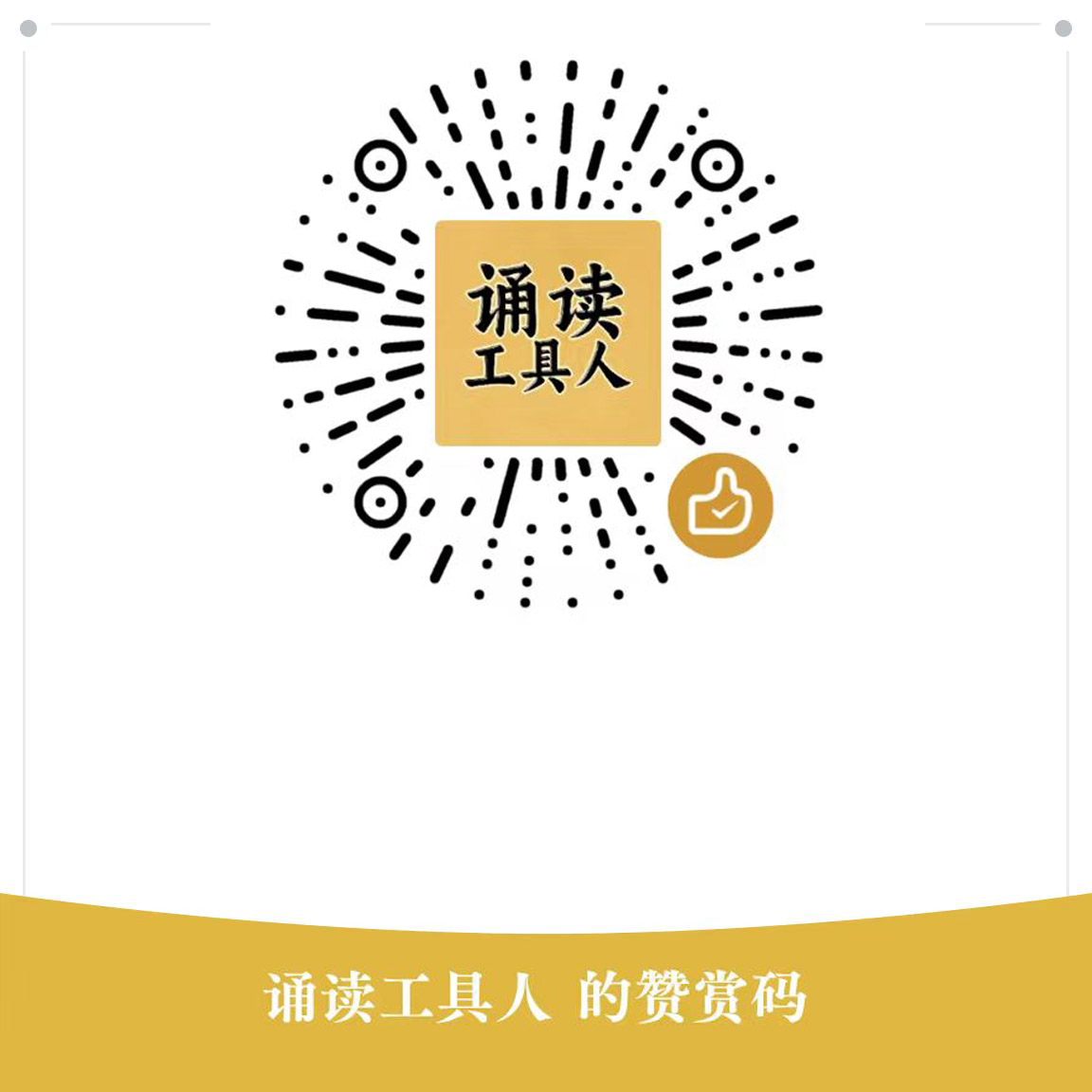小
中
大
录制于:2025年7月20日

仅永久VIP可访问

 0
27
0
0
27
0


确定要删除这条记录吗?此操作不可恢复。
编辑于:2025-08-24 14:24:46
拟古十二首
拼音译文音对译
正文字数:770
青天何历历,明星如白石。
黄姑与织女,相去不盈尺。
银河无鹊桥,非时将安适。
闺人理纨素,游子悲行役。
瓶冰知冬寒,霜露欺远客。
客似秋叶飞,飘飖不言归。
别后罗带长,愁宽去时衣。
乘月托宵梦,因之寄金徽。
高楼入青天,下有白玉堂。
明月看欲堕,当窗悬清光。
遥夜一美人,罗衣沾秋霜。
含情弄柔瑟,弹作陌上桑。
弦声何激烈,风卷绕飞梁。
行人皆踯躅,栖鸟起回翔。
但写妾意苦,莫辞此曲伤。
愿逢同心者,飞作紫鸳鸯。
长绳难系日,自古共悲辛。
黄金高北斗,不惜买阳春。
石火无留光,还如世中人。
即事已如梦,后来我谁身。
提壶莫辞贫,取酒会四邻。
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
清都绿玉树,灼烁瑶台春。
攀花弄秀色,远赠天仙人。
香风送紫蕊,直到扶桑津。
取掇世上艳,所贵心之珍。
相思传一笑,聊欲示情亲。
今日风日好,明日恐不如。
春风笑于人,何乃愁自居。
吹箫舞彩凤,酌醴鲙神鱼。
千金买一醉,取乐不求馀。
达士遗天地,东门有二疏。
愚夫同瓦石,有才知卷舒。
无事坐悲苦,块然涸辙鲋。
运速天地闭,胡风结飞霜。
百草死冬月,六龙颓西荒。
太白出东方,彗星扬精光。
鸳鸯非越鸟,何为眷南翔。
惟昔鹰将犬,今为侯与王。
得水成蛟龙,争池夺凤凰。
北斗不酌酒,南箕空簸扬。
世路今太行,回车竟何托。
万族皆凋枯,遂无少可乐。
旷野多白骨,幽魂共销铄。
荣贵当及时,春华宜照灼。
人非昆山玉,安得长璀错。
身没期不朽,荣名在麟阁。
月色不可扫,客愁不可道。
玉露生秋衣,流萤飞百草。
日月终销毁,天地同枯槁。
蟪蛄啼青松,安见此树老。
金丹宁误俗,昧者难精讨。
尔非千岁翁,多恨去世早。
饮酒入玉壶,藏身以为宝。
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
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
月兔空捣药,扶桑已成薪。
白骨寂无言,青松岂知春。
前后更叹息,浮荣安足珍。
仙人骑彩凤,昨下阆风岑。
海水三清浅,桃源一见寻。
遗我绿玉杯,兼之紫琼琴。
杯以倾美酒,琴以闲素心。
二物非世有,何论珠与金。
琴弹松里风,杯劝天上月。
风月长相知,世人何倏忽。
涉江弄秋水,爱此荷花鲜。
攀荷弄其珠,荡漾不成圆。
佳人彩云里,欲赠隔远天。
相思无由见,怅望凉风前。
去去复去去,辞君还忆君。
汉水既殊流,楚山亦此分。
人生难称意,岂得长为群。
越燕喜海日,燕鸿思朔云。
别久容华晚,琅玕不能饭。
日落知天昏,梦长觉道远。
望夫登高山,化石竟不返。
qīng tiān hé lì lì míng xīng rú bái shí
huáng gū yǔ zhī nǚ xiāng qù bù yíng chǐ
yín hé wú què qiáo fēi shí jiāng ān shì
guī rén lǐ wán sù yóu zǐ bēi xíng yì
píng bīng zhī dōng hán shuāng lù qī yuǎn kè
kè sì qiū yè fēi piāo yáo bù yán guī
bié hòu luó dài cháng chóu kuān qù shí yī
chéng yuè tuō xiāo mèng yīn zhī jì jīn huī
gāo lóu rù qīng tiān xià yǒu bái yù táng
míng yuè kàn yù duò dāng chuāng xuán qīng guāng
yáo yè yì měi rén luó yī zhān qiū shuāng
hán qíng nòng róu sè tán zuò mò shàng sāng
xián shēng hé jī liè fēng juǎn rào fēi liáng
xíng rén jiē zhí zhú qī niǎo qǐ huí xiáng
dàn xiě qiè yì kǔ mò cí cǐ qǔ shāng
yuàn féng tóng xīn zhě fēi zuò zǐ yuān yāng
cháng shéng nán xì rì zì gǔ gòng bēi xīn
huáng jīn gāo běi dǒu bù xī mǎi yáng chūn
shí huǒ wú liú guāng hái rú shì zhōng rén
jí shì yǐ rú mèng hòu lái wǒ shuí shēn
tí hú mò cí pín qǔ jiǔ huì sì lín
xiān rén shū huǎng hū wèi ruò zuì zhōng zhēn
qīng dū lǜ yù shù zhuó shuò yáo tái chūn
pān huā nòng xiù sè yuǎn zèng tiān xiān rén
xiāng fēng sòng zǐ ruǐ zhí dào fú sāng jīn
qǔ duō shì shàng yàn suǒ guì xīn zhī zhēn
xiāng sī chuán yí xiào liáo yù shì qíng qīn
jīn rì fēng rì hǎo míng rì kǒng bù rú
chūn fēng xiào yú rén hé nǎi chóu zì jū
chuī xiāo wǔ cǎi fèng zhuó lǐ kuài shén yú
qiān jīn mǎi yí zuì qǔ lè bù qiú yú
dá shì yí tiān dì dōng mén yǒu èr shū
yú fū tóng wǎ shí yǒu cái zhī juǎn shū
wú shì zuò bēi kǔ kuài rán hé zhé fù
yùn sù tiān dì bì hú fēng jié fēi shuāng
bǎi cǎo sǐ dōng yuè liù lóng tuí xī huāng
tài bái chū dōng fāng huì xīng yáng jīng guāng
yuān yāng fēi yuè niǎo hé wéi juàn nán xiáng
wéi xī yīng jiāng quǎn jīn wéi hóu yǔ wáng
dé shuǐ chéng jiāo lóng zhēng chí duó fèng huáng
běi dǒu bù zhuó jiǔ nán jī kōng bǒ yáng
shì lù jīn tài háng huí chē jìng hé tuō
wàn zú jiē diāo kū suì wú shǎo kě lè
kuàng yě duō bái gǔ yōu hún gòng xiāo shuò
róng guì dāng jí shí chūn huá yí zhào zhuó
rén fēi kūn shān yù ān dé cháng cuǐ cuò
shēn mò qī bù xiǔ róng míng zài lín gé
yuè sè bù kě sǎo kè chóu bù kě dào
yù lù shēng qiū yī liú yíng fēi bǎi cǎo
rì yuè zhōng xiāo huǐ tiān dì tóng kū gǎo
huì gū tí qīng sōng ān jiàn cǐ shù lǎo
jīn dān nìng wù sú mèi zhě nán jīng tǎo
ěr fēi qiān suì wēng duō hèn qù shì zǎo
yǐn jiǔ rù yù hú cáng shēn yǐ wéi bǎo
shēng zhě wéi guò kè sǐ zhě wéi guī rén
tiān dì yí nì lǚ tóng bēi wàn gǔ chén
yuè tù kōng dǎo yào fú sāng yǐ chéng xīn
bái gǔ jì wú yán qīng sōng qǐ zhī chūn
qián hòu gèng tàn xī fú róng ān zú zhēn
xiān rén qí cǎi fèng zuó xià làng fēng cén
hǎi shuǐ sān qīng qiǎn táo yuán yí jiàn xún
wèi wǒ lǜ yù bēi jiān zhī zǐ qióng qín
bēi yǐ qīng měi jiǔ qín yǐ xián sù xīn
èr wù fēi shì yǒu hé lùn zhū yǔ jīn
qín tán sōng lǐ fēng bēi quàn tiān shàng yuè
fēng yuè cháng xiāng zhī shì rén hé shū hū
shè jiāng nòng qiū shuǐ ài cǐ hé huā xiān
pān hé nòng qí zhū dàng yàng bù chéng yuán
jiā rén cǎi yún lǐ yù zèng gé yuǎn tiān
xiāng sī wú yóu jiàn chàng wàng liáng fēng qián
qù qù fù qù qù cí jūn hái yì jūn
hàn shuǐ jì shū liú chǔ shān yì cǐ fēn
rén shēng nán chèn yì qǐ dé cháng wéi qún
yuè yàn xǐ hǎi rì yàn hóng sī shuò yún
bié jiǔ róng huá wǎn láng gān bù néng fàn
rì luò zhī tiān hūn mèng cháng jué dào yuǎn
wàng fū dēng gāo shān huà shí jìng bù fǎn
青天何历历,明星如白石。
浩瀚的夜空,群星闪耀。
黄姑与织女,相去不盈尺。
银河无鹊桥,非时将安适。
闺人理纨素,游子悲行役。
瓶冰知冬寒,霜露欺远客。
客似秋叶飞,飘飖不言归。
别后罗带长,愁宽去时衣。
乘月托宵梦,因之寄金徽。
高楼入青天,下有白玉堂。
明月看欲堕,当窗悬清光。
遥夜一美人,罗衣沾秋霜。
含情弄柔瑟,弹作陌上桑。
弦声何激烈,风卷绕飞梁。
行人皆踯躅,栖鸟起回翔。
但写妾意苦,莫辞此曲伤。
愿逢同心者,飞作紫鸳鸯。
长绳难系日,自古共悲辛。
黄金高北斗,不惜买阳春。
石火无留光,还如世中人。
即事已如梦,后来我谁身。
提壶莫辞贫,取酒会四邻。
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
清都绿玉树,灼烁瑶台春。
攀花弄秀色,远赠天仙人。
香风送紫蕊,直到扶桑津。
取掇世上艳,所贵心之珍。
相思传一笑,聊欲示情亲。
今日风日好,明日恐不如。
春风笑于人,何乃愁自居。
吹箫舞彩凤,酌醴鲙神鱼。
千金买一醉,取乐不求馀。
达士遗天地,东门有二疏。
愚夫同瓦石,有才知卷舒。
无事坐悲苦,块然涸辙鲋。
运速天地闭,胡风结飞霜。
百草死冬月,六龙颓西荒。
太白出东方,彗星扬精光。
鸳鸯非越鸟,何为眷南翔。
惟昔鹰将犬,今为侯与王。
得水成蛟龙,争池夺凤凰。
北斗不酌酒,南箕空簸扬。
世路今太行,回车竟何托。
万族皆凋枯,遂无少可乐。
旷野多白骨,幽魂共销铄。
荣贵当及时,春华宜照灼。
人非昆山玉,安得长璀错。
身没期不朽,荣名在麟阁。
月色不可扫,客愁不可道。
玉露生秋衣,流萤飞百草。
日月终销毁,天地同枯槁。
蟪蛄啼青松,安见此树老。
金丹宁误俗,昧者难精讨。
尔非千岁翁,多恨去世早。
饮酒入玉壶,藏身以为宝。
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
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
天地之间如同一个旅店,可悲呵,人都将化为万古的尘埃。
月兔空捣药,扶桑已成薪。
白骨寂无言,青松岂知春。
前后更叹息,浮荣安足珍。
仙人骑彩凤,昨下阆风岑。
海水三清浅,桃源一见寻。
遗我绿玉杯,兼之紫琼琴。
杯以倾美酒,琴以闲素心。
二物非世有,何论珠与金。
琴弹松里风,杯劝天上月。
风月长相知,世人何倏忽。
涉江弄秋水,爱此荷花鲜。
攀荷弄其珠,荡漾不成圆。
佳人彩云里,欲赠隔远天。
美好的佳人藏在彩云里,要想赠给她鲜花,又远在天际。
相思无由见,怅望凉风前。
去去复去去,辞君还忆君。
汉水既殊流,楚山亦此分。
人生难称意,岂得长为群。
越燕喜海日,燕鸿思朔云。
别久容华晚,琅玕不能饭。
日落知天昏,梦长觉道远。
望夫登高山,化石竟不返。
lǐ bái nǐ gǔ shí èr shǒu
浩瀚的夜空,群星闪耀。
黄姑与织女,咫尺之内。
银河之上无喜鹊,不是七夕,可如何渡桥?
闺妇织锦于屋内,游子悲叹在行道。
瓶水结冰可见冬寒,远行的游子身受严霜凄寒之苦。
游子如同风中的秋叶,飘向四方,无处可归。
分别后,人因忧愁瘦损,罗带日长,衣裳渐宽。
趁着月色托之魂梦,把我的思念传到边关。
高楼耸入青天,下有白玉厅堂。
明月似欲下落,窗户上悬着它的清光。
长夜之中美人难眠,锦罗衣衫沾上了秋霜。
含情脉脉拨弄琴瑟,弹奏一曲《陌上桑》。
寄情深浓弦声凄切,风卷琴声绕梁不绝。
行人感怀驻步倾听,入巢鸟儿又展转回翔。
是我心情的悲苦,所以才有那曲调哀伤。
希望能够遇到知音,比翼双飞,作一对鸳鸯。
长绳难系西飞的白日,自古以来人们就为此而悲辛。
黄金堆积高过北斗,不惜买得阳春的光阴。
石头上的火花转歇便逝,正如世间的人。
往事流逝已如梦境,死去转世又会变成什么人?
提起酒壶,不要说贫,取酒设宴邀请四邻。
仙人的事情实在渺茫,不如豪饮大醉才是真。
清都的绿色玉树,闪耀着瑶台艳丽的春光。
折花欣赏那秀美的颜色,遥遥赠给天上的仙人。
幽香的和风带着紫色的花蕊,一直飘飞到日出的扶桑。
采掇世上的艳色,珍重心中的真诚。
相思时传去一笑,聊以表我想念的深情。
今日风光美好,明日恐怕就不及。
春风对人而笑,为何哀愁独居?
吹起萧声,似彩凤起舞,斟满美酒,脍好神鱼。
不辞千金买来一醉,只图欢乐何论其余。
旷达之士遗身天地之间,东宫门外二疏离朝而去。
愚人如同瓦石,圣贤才懂得曲伸。
不必独自悲苦,孑然独处,似那车辙里的枯鱼。
天地闭塞贤人潜隐,胡风为灾结成飞霜。
百草枯落于冬天,圣驾奔亡到边远的西荒。
太白星出于东方,彗星发出耀眼的精光。
鸳鸯本非越地的鸟,为什么又要飞向南方?
只为昔日的鹰与犬,而今都作了侯与王。
得水的变成蛟龙,争权夺利互不相让。
北斗为斗却不盛酒,南箕称箕空在簸扬。
世路艰难如同太行,路不可行,回车何托?
自古以来万物都要凋落枯死,从来世人难得暂时欢乐。
旷野处处堆满了白骨,幽灵孤魂也同沉没。
荣华富贵当及时,如同春花及时开放。
世人不是那昆山玉石,怎能如玉光永久闪熠?
身死期待声名不灭,早题英名在麒麟阁上。
满地月色不可扫除,游子哀愁难以倾吐。
秋衣已沾上玉露,草丛中流萤飞舞。
日月终将毁灭,天地自然也会凋枯。
寒蝉在青松树上哀鸣,它怎么能看到此树衰老?
即使金丹不能误人,愚昧的人也难以精心研讨。
你不是那千岁寿仙,徒然抱怨弃世太早。
不如饮酒,醉入这壶中天地,在其中藏身珍惜如宝。
活的人是世间过客,死去者为归家的人。
天地之间如同一个旅店,可悲呵,人都将化为万古的尘埃。
月中白兔徒然捣药,扶桑神木已变成了薪柴。
地下白骨寂寞无言,青松岂知冬去春来?
思前想后更加叹息不己,功名富贵不值得珍爱。
仙人驾着彩凤,刚从阆风山下凡。
他曾三次见到海水变浅,我们相遇在桃源。
赠我一只绿玉酒杯,还有一把紫琼琴。
杯子用来倾注美酒,琴声用以清闲本心。
这二物并非人世所有,珍珠金玉不能比拟。
在松林里迎风弹琴,在夜晚的清光中举杯遥劝明月。
清风朗月是我终生的知己,世间凡人的生命何等短促。
划船到江中去荡漾秋天的江水,更喜爱这荷花的鲜艳。
拨弄那荷叶上的水珠,滚动着却总不成圆。
美好的佳人藏在彩云里,要想赠给她鲜花,又远在天际。
苦苦相思而相见无期,惆怅遥望在凄凉的秋风里。
走了一程又一程,送你远行却又思念你。
汉水也会分流,楚山亦非一脉。
人生很难如意,哪能长久相伴?
越燕向往那大海上的太阳,燕鸿只牵挂着朔方的白云。
别离日久容颜衰老,虽有佳肴,却无心享用。
太阳西下知道日色已昏,归梦漫长更觉路途遥远。
登上高山极望丈夫,化成石头千古不返。
李白《拟古十二首》
1
00:00:00,000 --> 00:00:10,400
李白《拟古十二首》
2
00:00:10,400 --> 00:00:19,733
青天何历历,明星如白石。
3
00:00:19,733 --> 00:00:30,033
黄姑与织女,相去不盈尺。
4
00:00:30,033 --> 00:00:39,600
银河无鹊桥,非时将安适。
5
00:00:39,600 --> 00:00:50,133
闺人理纨素,游子悲行役。
6
00:00:50,133 --> 00:01:00,600
瓶冰知冬寒,霜露欺远客。
7
00:01:00,600 --> 00:01:12,133
客似秋叶飞,飘飖不言归。
8
00:01:12,133 --> 00:01:22,500
别后罗带长,愁宽去时衣。
9
00:01:22,500 --> 00:01:35,533
乘月托宵梦,因之寄金徽。
10
00:01:35,533 --> 00:01:45,333
高楼入青天,下有白玉堂。
11
00:01:45,333 --> 00:01:54,700
明月看欲堕,当窗悬清光。
12
00:01:54,700 --> 00:02:04,233
遥夜一美人,罗衣沾秋霜。
13
00:02:04,233 --> 00:02:15,166
含情弄柔瑟,弹作陌上桑。
14
00:02:15,166 --> 00:02:24,700
弦声何激烈,风卷绕飞梁。
15
00:02:24,700 --> 00:02:34,533
行人皆踯躅,栖鸟起回翔。
16
00:02:34,533 --> 00:02:45,800
但写妾意苦,莫辞此曲伤。
17
00:02:45,800 --> 00:02:57,800
愿逢同心者,飞作紫鸳鸯。
18
00:02:57,800 --> 00:03:07,533
长绳难系日,自古共悲辛。
19
00:03:07,533 --> 00:03:17,233
黄金高北斗,不惜买阳春。
20
00:03:17,233 --> 00:03:26,400
石火无留光,还如世中人。
21
00:03:26,400 --> 00:03:36,733
即事已如梦,后来我谁身。
22
00:03:36,733 --> 00:03:46,600
提壶莫辞贫,取酒会四邻。
23
00:03:46,600 --> 00:03:59,900
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
24
00:03:59,900 --> 00:04:08,800
清都绿玉树,灼烁瑶台春。
25
00:04:08,800 --> 00:04:18,933
攀花弄秀色,远赠天仙人。
26
00:04:18,933 --> 00:04:28,566
香风送紫蕊,直到扶桑津。
27
00:04:28,566 --> 00:04:38,766
取掇世上艳,所贵心之珍。
28
00:04:38,766 --> 00:04:50,733
相思传一笑,聊欲示情亲。
29
00:04:50,733 --> 00:04:58,900
今日风日好,明日恐不如。
30
00:04:58,900 --> 00:05:07,600
春风笑于人,何乃愁自居。
31
00:05:07,600 --> 00:05:15,900
吹箫舞彩凤,酌醴鲙神鱼。
32
00:05:15,900 --> 00:05:25,100
千金买一醉,取乐不求馀。
33
00:05:25,100 --> 00:05:34,100
达士遗天地,东门有二疏。
34
00:05:34,100 --> 00:05:43,333
愚夫同瓦石,有才知卷舒。
35
00:05:43,333 --> 00:05:54,800
无事坐悲苦,块然涸辙鲋。
36
00:05:54,800 --> 00:06:03,133
运速天地闭,胡风结飞霜。
37
00:06:03,133 --> 00:06:12,333
百草死冬月,六龙颓西荒。
38
00:06:12,333 --> 00:06:20,800
太白出东方,彗星扬精光。
39
00:06:20,800 --> 00:06:29,900
鸳鸯非越鸟,何为眷南翔。
40
00:06:29,900 --> 00:06:39,033
惟昔鹰将犬,今为侯与王。
41
00:06:39,033 --> 00:06:48,166
得水成蛟龙,争池夺凤凰。
42
00:06:48,166 --> 00:06:58,433
北斗不酌酒,南箕空簸扬。
43
00:06:58,433 --> 00:07:07,933
世路今太行,回车竟何托。
44
00:07:07,933 --> 00:07:17,500
万族皆凋枯,遂无少可乐。
45
00:07:17,500 --> 00:07:27,633
旷野多白骨,幽魂共销铄。
46
00:07:27,633 --> 00:07:36,633
荣贵当及时,春华宜照灼。
47
00:07:36,633 --> 00:07:44,966
人非昆山玉,安得长璀错。
48
00:07:44,966 --> 00:07:54,900
身没期不朽,荣名在麟阁。
49
00:07:54,900 --> 00:08:04,333
月色不可扫,客愁不可道。
50
00:08:04,333 --> 00:08:13,966
玉露生秋衣,流萤飞百草。
51
00:08:13,966 --> 00:08:24,300
日月终销毁,天地同枯槁。
52
00:08:24,300 --> 00:08:33,566
蟪蛄啼青松,安见此树老。
53
00:08:33,566 --> 00:08:42,566
金丹宁误俗,昧者难精讨。
54
00:08:42,566 --> 00:08:52,033
尔非千岁翁,多恨去世早。
55
00:08:52,033 --> 00:09:05,533
饮酒入玉壶,藏身以为宝。
56
00:09:05,533 --> 00:09:15,400
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
57
00:09:15,400 --> 00:09:26,766
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
58
00:09:26,766 --> 00:09:36,966
月兔空捣药,扶桑已成薪。
59
00:09:36,966 --> 00:09:48,166
白骨寂无言,青松岂知春。
60
00:09:48,166 --> 00:10:01,500
前后更叹息,浮荣安足珍。
61
00:10:01,500 --> 00:10:11,200
仙人骑彩凤,昨下阆风岑。
62
00:10:11,200 --> 00:10:19,366
海水三清浅,桃源一见寻。
63
00:10:19,366 --> 00:10:27,700
遗我绿玉杯,兼之紫琼琴。
64
00:10:27,700 --> 00:10:35,633
杯以倾美酒,琴以闲素心。
65
00:10:35,633 --> 00:10:44,633
二物非世有,何论珠与金。
66
00:10:44,633 --> 00:10:51,800
琴弹松里风,杯劝天上月。
67
00:10:51,800 --> 00:11:05,966
风月长相知,世人何倏忽。
68
00:11:05,966 --> 00:11:16,600
涉江弄秋水,爱此荷花鲜。
69
00:11:16,600 --> 00:11:26,633
攀荷弄其珠,荡漾不成圆。
70
00:11:26,633 --> 00:11:36,833
佳人彩云里,欲赠隔远天。
71
00:11:36,833 --> 00:11:50,900
相思无由见,怅望凉风前。
72
00:11:50,900 --> 00:12:02,300
去去复去去,辞君还忆君。
73
00:12:02,300 --> 00:12:14,600
汉水既殊流,楚山亦此分。
74
00:12:14,600 --> 00:12:25,566
人生难称意,岂得长为群。
75
00:12:25,566 --> 00:12:35,733
越燕喜海日,燕鸿思朔云。
76
00:12:35,733 --> 00:12:46,900
别久容华晚,琅玕不能饭。
77
00:12:46,900 --> 00:12:59,800
日落知天昏,梦长觉道远。
78
00:12:59,800 --> 00:13:10,500
望夫登高山,化石竟不返。
唐代
táng dà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