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中
大
录制于:2025年7月20日

仅永久VIP可访问

 0
25
0
0
25
0


确定要删除这条记录吗?此操作不可恢复。
编辑于:2025-08-02 15:17:00
感遇诗三十八首
拼音译文音对译
正文字数:1990
微月生西海,幽阳始代升。
圆光正东满,阴魄已朝凝。
太极生天地,三元更废兴。
至精谅斯在,三五谁能征。
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
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
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
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
苍苍丁零塞,今古缅荒途。
亭堠何摧兀,暴骨无全躯。
黄沙幕南起,白日隐西隅。
汉甲三十万,曾以事匈奴。
但见沙场死,谁怜塞上孤。
乐羊为魏将,食子殉军功。
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
吾闻中山相,乃属放麑翁。
孤兽犹不忍,况以奉君终。
市人矜巧智,于道若童蒙。
倾夺相夸侈,不知身所终。
曷见玄真子,观世玉壶中。
窅然遗天地,乘化入无穷。
吾观龙变化,乃知至阳精。
石林何冥密,幽洞无留行。
古之得仙道,信与元化并。
玄感非象识,谁能测沈冥。
世人拘目见,酣酒笑丹经。
昆仑有瑶树,安得采其英。
白日每不归,青阳时暮矣。
茫茫吾何思,林卧观无始。
众芳委时晦,鶗鴂鸣悲耳。
鸿荒古已颓,谁识巢居子。
吾观昆仑化,日月沦洞冥。
精魄相交会,天壤以罗生。
仲尼推太极,老聃贵窈冥。
西方金仙子,崇义乃无明。
空色皆寂灭,缘业定何成。
名教信纷藉,死生俱未停。
圣人秘元命,惧世乱其真。
如何嵩公辈,诙谲误时人。
先天诚为美,阶乱祸谁因。
长城备胡寇,嬴祸发其亲。
赤精既迷汉,子年何救秦。
去去桃李花,多言死如麻。
深居观元化,悱然争朵颐。
谗说相啖食,利害纷㘈㘈。
便便夸毗子,荣耀更相持。
务光让天下,商贾竞刀锥。
已矣行采芝,万世同一时。
吾爱鬼谷子,青溪无垢氛。
囊括经世道,遗身在白云。
七雄方龙斗,天下久无君。
浮荣不足贵,遵养晦时文。
舒可弥宇宙,卷之不盈分。
岂徒山木寿,空与麋鹿群。
呦呦南山鹿,罹罟以媒和。
招摇青桂树,幽蠹亦成科。
世情甘近习,荣耀纷如何。
怨憎未相复,亲爱生祸罗。
瑶台倾巧笑,玉杯殒双蛾。
谁见枯城蘖,青青成斧柯。
林居病时久,水木澹孤清。
闲卧观物化,悠悠念无生。
青春始萌达。朱火已满盈。
徂落方自此,感叹何时平。
临歧泣世道,天命良悠悠。
昔日殷王子,玉马遂朝周。
宝鼎沦伊谷,瑶台成古丘。
西山伤遗老,东陵有故侯。
贵人难得意,赏爱在须臾。
莫以心如玉,探他明月珠。
昔称夭桃子,今为舂市徒。
鸱鸮悲东国,麋鹿泣姑苏。
谁见鸱夷子,扁舟去五湖。
圣人去已久,公道缅良难。
蚩蚩夸毗子,尧禹以为谩。
骄荣贵工巧。势利迭相干。
燕王尊乐毅,分国愿同欢。
鲁连让齐爵,遗组去邯郸。
伊人信往矣,感激为谁叹。
幽居观天运,悠悠念群生。
终古代兴没,豪圣莫能争。
三季沦周赧,七雄灭秦嬴。
复闻赤精子,提剑入咸京。
炎光既无象,晋虏复纵横。
尧禹道已昧,昏虐势方行。
岂无当世雄,天道与胡兵。
咄咄安可言,时醉而未醒。
仲尼溺东鲁,伯阳遁西溟。
大运自古来,旅人胡叹哉。
逶迤势已久,骨鲠道斯穷。
岂无感激者,时俗颓此风。
灌园何其鄙,皎皎於陵中。
世道不相容,喈喈张长公。
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
黄屋非尧意,瑶台安可论。
吾闻西方化,清净道弥敦。
奈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
云构山林尽,瑶图珠翠烦。
鬼工尚未可,人力安能存。
夸愚适增累,矜智道逾昏。
玄天幽且默,群议曷嗤嗤。
圣人教犹在,世运久陵夷。
一绳将何系,忧醉不能持。
去去行采芝,勿为尘所欺。
蜻蛉游天地,与世本无患。
飞飞未能止,黄雀来相干。
穰侯富秦宠,金石比交欢。
出入咸阳里,诸侯莫敢言。
宁知山东客,激怒秦王肝。
布衣取丞相,千载为辛酸。
微霜知岁晏,斧柯始青青。
况乃金天夕,浩露沾群英。
登山望宇宙,白日已西暝。
云海方荡潏,孤鳞安得宁。
翡翠巢南海,雄雌珠树林。
何知美人意,骄爱比黄金。
杀身炎州里,委羽玉堂阴。
旖旎光首饰,葳蕤烂锦衾。
岂不在遐远,虞罗忽见寻。
多材信为累,叹息此珍禽。
挈瓶者谁子,姣服当青春。
三五明月满,盈盈不自珍。
高堂委金玉,微缕悬千钧。
如何负公鼎,被夺笑时人。
玄蝉号白露,兹岁已蹉跎。
群物从大化,孤英将奈何。
瑶台有青鸟,远食玉山禾。
昆仑见玄凤,岂复虞云罗。
荒哉穆天子,好与白云期。
宫女多怨旷,层城闭蛾眉。
日耽瑶池乐,岂伤桃李时。
青苔空萎绝,白发生罗帷。
朝发宜都渚,浩然思故乡。
故乡不可见,路隔巫山阳。
巫山彩云没,高丘正微茫。
伫立望已久,涕落沾衣裳。
岂兹越乡感,忆昔楚襄王。
朝云无处所,荆国亦沦亡。
昔日章华宴,荆王乐荒淫。
霓旌翠羽盖,射兕云梦林。
朅来高唐观,怅望云阳岑。
雄图今何在,黄雀空哀吟。
丁亥岁云暮,西山事甲兵。
赢粮匝邛道,荷戟争羌城。
严冬阴风劲,穷岫泄云生。
昏曀无昼夜,羽檄复相惊。
拳局竞万仞,崩危走九冥。
籍籍峰壑里,哀哀冰雪行。
圣人御宇宙,闻道泰阶平。
肉食谋何失,藜藿缅纵横。
可怜瑶台树,灼灼佳人姿。
碧华映朱实,攀折青春时。
岂不盛光宠,荣君白玉墀。
但恨红芳歇,凋伤感所思。
朅来豪游子,势利祸之门。
如何兰膏叹,感激自生冤。
众趋明所避,时弃道犹存。
云渊既已失,罗网与谁论。
箕山有高节,湘水有清源。
唯应白鸥鸟,可为洗心言。
索居犹几日,炎夏忽然衰。
阳彩皆阴翳,亲友尽睽违。
登山望不见,涕泣久涟洏。
宿梦感颜色,若与白云期。
马上骄豪子,驱逐正蚩蚩。
蜀山与楚水,携手在何时。
金鼎合神丹,世人将见欺。
飞飞骑羊子,胡乃在峨眉。
变化固幽类,芳菲能几时。
疲疴苦沦世,忧痗日侵淄。
眷然顾幽褐,白云空涕洟。
朔风吹海树,萧条边已秋。
亭上谁家子,哀哀明月楼。
自言幽燕客,结发事远游。
赤丸杀公吏,白刃报私仇。
避仇至海上,被役此边州。
故乡三千里,辽水复悠悠。
每愤胡兵入,常为汉国羞。
何知七十战,白首未封侯。
本为贵公子,平生实爱才。
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
西驰丁零塞,北上单于台。
登山见千里,怀古心悠哉。
谁言未亡祸,磨灭成尘埃。
浩然坐何慕,吾蜀有峨眉。
念与楚狂子,悠悠白云期。
时哉悲不会,涕泣久涟洏。
梦登绥山穴,南采巫山芝。
探元观群化,遗世从云螭。
婉娈时永矣,感悟不见之。
朝入云中郡,北望单于台,
胡秦何密迩,沙朔气雄哉。
藉藉天骄子,猖狂已复来。
塞垣无名将,亭堠空崔嵬。
咄嗟吾何叹,边人涂草莱。
仲尼探元化,幽鸿顺阳和。
大运自盈缩,春秋递来过。
盲飙忽号怒,万物相纷劘。
溟海皆震荡,孤凤其如何。
wēi yuè shēng xī hǎi yōu yáng shǐ dài shēng
yuán guāng zhèng dōng mǎn yīn pò yǐ zhāo níng
tài jí shēng tiān dì sān yuán gēng fèi xīng
zhì jīng liàng sī zài sān wǔ shuí néng zhēng
lán ruò shēng chūn xià qiān wèi hé qīng qīng
yōu dú kōng lín sè zhū ruí mào zǐ jīng
chí chí bái rì wǎn niǎo niǎo qiū fēng shēng
suì huá jìn yáo luò fāng yì jìng hé chéng
cāng cāng dīng líng sài jīn gǔ miǎn huāng tú
tíng hòu hé cuī wù pù gǔ wú quán qū
huáng shā mù nán qǐ bái rì yǐn xī yú
hàn jiǎ sān shí wàn céng yǐ shì xiōng nú
dàn jiàn shā chǎng sǐ shuí lián sài shàng gū
yuè yáng wéi wèi jiàng shí zǐ xùn jūn gōng
gǔ ròu qiě xiāng bó tā rén ān dé zhōng
wú wén zhōng shān xiàng nǎi zhǔ fàng ní wēng
gū shòu yóu bù rěn kuàng yǐ fèng jūn zhōng
shì rén jīn qiǎo zhì yú dào ruò tóng méng
qīng duó xiāng kuā chǐ bù zhī shēn suǒ zhōng
hé jiàn xuán zhēn zǐ guān shì yù hú zhōng
yǎo rán yí tiān dì chéng huà rù wú qióng
wú guān lóng biàn huà nǎi zhī zhì yáng jīng
shí lín hé míng mì yōu dòng wú liú xíng
gǔ zhī dé xiān dào xìn yǔ yuán huà bìng
xuán gǎn fēi xiàng shí shuí néng cè chén míng
shì rén jū mù jiàn hān jiǔ xiào dān jīng
kūn lún yǒu yáo shù ān dé cǎi qí yīng
bái rì měi bù guī qīng yáng shí mù yǐ
máng máng wú hé sī lín wò guān wú shǐ
zhòng fāng wěi shí huì tí jué míng bēi ěr
hóng huāng gǔ yǐ tuí shuí shí cháo jū zǐ
wú guān kūn lún huà rì yuè lún dòng míng
jīng pò xiāng jiāo huì tiān rǎng yǐ luó shēng
zhòng ní tuī tài jí lǎo dān guì yǎo míng
xī fāng jīn xiān zǐ chóng yì nǎi wú míng
kōng sè jiē jì miè yuán yè dìng hé chéng
míng jiào xìn fēn jiè sǐ shēng jù wèi tíng
shèng rén mì yuán mìng jù shì luàn qí zhēn
rú hé sōng gōng bèi huī jué wù shí rén
xiān tiān chéng wéi měi jiē luàn huò shuí yīn
cháng chéng bèi hú kòu yíng huò fā qí qīn
chì jīng jì mí hàn zǐ nián hé jiù qín
qù qù táo lǐ huā duō yán sǐ rú má
shēn jū guān yuán huà fěi rán zhēng duǒ yí
chán shuō xiāng dàn shí lì hài fēn yì㘈yì㘈
pián pián kuā pí zǐ róng yào gèng xiāng chí
wù guāng ràng tiān xià shāng gǔ jìng dāo zhuī
yǐ yǐ xíng cǎi zhī wàn shì tóng yì shí
wú ài guǐ gǔ zǐ qīng xī wú gòu fēn
náng kuò jīng shì dào yí shēn zài bái yún
qī xióng fāng lóng dòu tiān xià jiǔ wú jūn
fú róng bù zú guì zūn yǎng huì shí wén
shū kě mí yǔ zhòu juǎn zhī bù yíng fēn
qǐ tú shān mù shòu kōng yǔ mí lù qún
yōu yōu nán shān lù lí gǔ yǐ méi hé
zhāo yáo qīng guì shù yōu dù yì chéng kē
shì qíng gān jìn xí róng yào fēn rú hé
yuàn zēng wèi xiāng fù qīn ài shēng huò luó
yáo tái qīng qiǎo xiào yù bēi yǔn shuāng é
shuí jiàn kū chéng niè qīng qīng chéng fǔ kē
lín jū bìng shí jiǔ shuǐ mù dàn gū qīng
xián wò guān wù huà yōu yōu niàn wú shēng
qīng chūn shǐ méng dá zhū huǒ yǐ mǎn yíng
cú luò fāng zì cǐ gǎn tàn hé shí píng
lín qí qì shì dào tiān mìng liáng yōu yōu
xī rì yīn wáng zǐ yù mǎ suì cháo zhōu
bǎo dǐng lún yī gǔ yáo tái chéng gǔ qiū
xī shān shāng yí lǎo dōng líng yǒu gù hóu
guì rén nán dé yì shǎng ài zài xū yú
mò yǐ xīn rú yù tàn tā míng yuè zhū
xī chēng yāo táo zǐ jīn wéi chōng shì tú
chī xiāo bēi dōng guó mí lù qì gū sū
shuí jiàn chī yí zǐ piān zhōu qù wǔ hú
shèng rén qù yǐ jiǔ gōng dào miǎn liáng nán
chī chī kuā pí zǐ yáo yǔ yǐ wéi màn
jiāo róng guì gōng qiǎo shì lì dié xiāng gān
yān wáng zūn yuè yì fēn guó yuàn tóng huān
lǔ lián ràng qí jué yí zǔ qù hán dān
yī rén xìn wǎng yǐ gǎn jī wèi shuí tàn
yōu jū guān tiān yùn yōu yōu niàn qún shēng
zhōng gǔ dài xīng mò háo shèng mò néng zhēng
sān jì lún zhōu nǎn qī xióng miè qín yíng
fù wén chì jīng zǐ tí jiàn rù xián jīng
yán guāng jì wú xiàng jìn lǔ fù zòng héng
yáo yǔ dào yǐ mèi hūn nüè shì fāng xíng
qǐ wú dāng shì xióng tiān dào yǔ hú bīng
duō duō ān kě yán shí zuì ér wèi xǐng
zhòng ní nì dōng lǔ bó yáng dùn xī míng
dà yùn zì gǔ lái lǚ rén hú tàn zāi
wēi yí shì yǐ jiǔ gǔ gěng dào sī qióng
qǐ wú gǎn jī zhě shí sú tuí cǐ fēng
guàn yuán hé qí bǐ jiǎo jiǎo wū líng zhōng
shì dào bù xiāng róng jiē jiē zhāng cháng gōng
shèng rén bú lì jǐ yōu jì zài yuán yuán
huáng wū fēi yáo yì yáo tái ān kě lùn
wú wén xī fāng huà qīng jìng dào mí dūn
nài hé qióng jīn yù diāo kè yǐ wéi zūn
yún gòu shān lín jìn yáo tú zhū cuì fán
guǐ gōng shàng wèi kě rén lì ān néng cún
kuā yú shì zēng lèi jīn zhì dào yú hūn
xuán tiān yōu qiě mò qún yì hé chī chī
shèng rén jiào yóu zài shì yùn jiǔ líng yí
yì shéng jiāng hé xì yōu zuì bù néng chí
qù qù xíng cǎi zhī wù wéi chén suǒ qī
qīng líng yóu tiān dì yǔ shì běn wú huàn
fēi fēi wèi néng zhǐ huáng què lái xiāng gān
rǎng hóu fù qín chǒng jīn shí bǐ jiāo huān
chū rù xián yáng lǐ zhū hóu mò gǎn yán
nìng zhī shān dōng kè jī nù qín wáng gān
bù yī qǔ chéng xiàng qiān zǎi wéi xīn suān
wēi shuāng zhī suì yàn fǔ kē shǐ qīng qīng
kuàng nǎi jīn tiān xī hào lù zhān qún yīng
dēng shān wàng yǔ zhòu bái rì yǐ xī míng
yún hǎi fāng dàng yù gū lín ān dé níng
fěi cuì cháo nán hǎi xióng cí zhū shù lín
hé zhī měi rén yì jiāo ài bǐ huáng jīn
shā shēn yán zhōu lǐ wěi yǔ yù táng yīn
yǐ nǐ guāng shǒu shì wēi ruí làn jǐn qīn
qǐ bú zài xiá yuǎn yú luó hū jiàn xún
duō cái xìn wéi lèi tàn xī cǐ zhēn qín
qiè píng zhě shuí zǐ jiāo fú dāng qīng chūn
sān wǔ míng yuè mǎn yíng yíng bú zì zhēn
gāo táng wěi jīn yù wēi lǚ xuán qiān jūn
rú hé fù gōng dǐng bèi duó xiào shí rén
xuán chán hào bái lù zī suì yǐ cuō tuó
qún wù cóng dà huà gū yīng jiāng nài hé
yáo tái yǒu qīng niǎo yuǎn shí yù shān hé
kūn lún jiàn xuán fèng qǐ fù yú yún luó
huāng zāi mù tiān zǐ hào yǔ bái yún qī
gōng nǚ duō yuàn kuàng céng chéng bì é méi
rì dān yáo chí lè qǐ shāng táo lǐ shí
qīng tái kōng wěi jué bái fà shēng luó wéi
zhāo fā yí dū zhǔ hào rán sī gù xiāng
gù xiāng bù kě jiàn lù gé wū shān yáng
wū shān cǎi yún mò gāo qiū zhèng wēi máng
zhù lì wàng yǐ jiǔ tì luò zhān yī cháng
qǐ zī yuè xiāng gǎn yì xī chǔ xiāng wáng
zhāo yún wú chù suǒ jīng guó yì lún wáng
xī rì zhāng huá yàn jīng wáng lè huāng yín
ní jīng cuì yǔ gài shè sì yún mèng lín
qiè lái gāo táng guān chàng wàng yún yáng cén
xióng tú jīn hé zài huáng què kōng āi yín
dīng hài suì yún mù xī shān shì jiǎ bīng
yíng liáng zā qióng dào hè jǐ zhēng qiāng chéng
yán dōng yīn fēng jìng qióng xiù xiè yún shēng
hūn yì wú zhòu yè yǔ xí fù xiāng jīng
quán jú jìng wàn rèn bēng wēi zǒu jiǔ míng
jí jí fēng hè lǐ āi āi bīng xuě xíng
shèng rén yù yǔ zhòu wén dào tài jiē píng
ròu shí móu hé shī lí huò miǎn zòng héng
kě lián yáo tái shù zhuó zhuó jiā rén zī
bì huá yìng zhū shí pān zhé qīng chūn shí
qǐ bú shèng guāng chǒng róng jūn bái yù chí
dàn hèn hóng fāng xiē diāo shāng gǎn suǒ sī
qiè lái háo yóu zǐ shì lì huò zhī mén
rú hé lán gāo tàn gǎn jī zì shēng yuān
zhòng qū míng suǒ bì shí qì dào yóu cún
yún yuān jì yǐ shī luó wǎng yǔ shuí lùn
jī shān yǒu gāo jié xiāng shuǐ yǒu qīng yuán
wéi yīng bái ōu niǎo kě wèi xǐ xīn yán
suǒ jū yóu jǐ rì yán xià hū rán shuāi
yáng cǎi jiē yīn yì qīn yǒu jìn kuí wéi
dēng shān wàng bú jiàn tì qì jiǔ lián ér
sù mèng gǎn yán sè ruò yǔ bái yún qī
mǎ shàng jiāo háo zǐ qū zhú zhèng chī chī
shǔ shān yǔ chǔ shuǐ xié shǒu zài hé shí
jīn dǐng hé shén dān shì rén jiāng jiàn qī
fēi fēi qí yáng zǐ hú nǎi zài é méi
biàn huà gù yōu lèi fāng fēi néng jǐ shí
pí kē kǔ lún shì yōu mèi rì qīn zī
juàn rán gù yōu hè bái yún kōng tì yí
shuò fēng chuī hǎi shù xiāo tiáo biān yǐ qiū
tíng shàng shuí jiā zǐ āi āi míng yuè lóu
zì yán yōu yān kè jié fà shì yuǎn yóu
chì wán shā gōng lì bái rèn bào sī chóu
bì chóu zhì hǎi shàng bèi yì cǐ biān zhōu
gù xiāng sān qiān lǐ liáo shuǐ fù yōu yōu
měi fèn hú bīng rù cháng wèi hàn guó xiū
hé zhī qī shí zhàn bái shǒu wèi fēng hóu
běn wéi guì gōng zǐ píng shēng shí ài cái
gǎn shí sī bào guó bá jiàn qǐ hāo lái
xī chí dīng líng sài běi shàng chán yú tái
dēng shān jiàn qiān lǐ huái gǔ xīn yōu zāi
shuí yán wèi wáng huò mó miè chéng chén āi
hào rán zuò hé mù wú shǔ yǒu é méi
niàn yǔ chǔ kuáng zǐ yōu yōu bái yún qī
shí zāi bēi bú huì tì qì jiǔ lián ér
mèng dēng suí shān xué nán cǎi wū shān zhī
tàn yuán guān qún huà yí shì cóng yún chī
wǎn luán shí yǒng yǐ gǎn wù bú jiàn zhī
zhāo rù yún zhōng jùn běi wàng chán yú tái
hú qín hé mì ěr shā shuò qì xióng zāi
jí jí tiān jiāo zǐ chāng kuáng yǐ fù lái
sài yuán wú míng jiàng tíng hòu kōng cuī wéi
duō jiē wú hé tàn biān rén tú cǎo lái
zhòng ní tàn yuán huà yōu hóng shùn yáng hé
dà yùn zì yíng suō chūn qiū dì lái guò
máng biāo hū háo nù wàn wù xiāng fēn mó
míng hǎi jiē zhèn dàng gū fèng qí rú hé
微月生西海,幽阳始代升。
月牙儿在西海开始生长,隐没的太阳就变化上升。
圆光正东满,阴魄已朝凝。
太极生天地,三元更废兴。
至精谅斯在,三五谁能征。
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
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
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
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
苍苍丁零塞,今古缅荒途。
亭堠何摧兀,暴骨无全躯。
黄沙幕南起,白日隐西隅。
汉甲三十万,曾以事匈奴。
但见沙场死,谁怜塞上孤。
乐羊为魏将,食子殉军功。
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
吾闻中山相,乃属放麑翁。
孤兽犹不忍,况以奉君终。
市人矜巧智,于道若童蒙。
倾夺相夸侈,不知身所终。
曷见玄真子,观世玉壶中。
窅然遗天地,乘化入无穷。
吾观龙变化,乃知至阳精。
石林何冥密,幽洞无留行。
古之得仙道,信与元化并。
玄感非象识,谁能测沈冥。
世人拘目见,酣酒笑丹经。
昆仑有瑶树,安得采其英。
白日每不归,青阳时暮矣。
茫茫吾何思,林卧观无始。
众芳委时晦,鶗鴂鸣悲耳。
鸿荒古已颓,谁识巢居子。
吾观昆仑化,日月沦洞冥。
精魄相交会,天壤以罗生。
仲尼推太极,老聃贵窈冥。
西方金仙子,崇义乃无明。
空色皆寂灭,缘业定何成。
名教信纷藉,死生俱未停。
圣人秘元命,惧世乱其真。
如何嵩公辈,诙谲误时人。
先天诚为美,阶乱祸谁因。
长城备胡寇,嬴祸发其亲。
赤精既迷汉,子年何救秦。
去去桃李花,多言死如麻。
深居观元化,悱然争朵颐。
谗说相啖食,利害纷㘈㘈。
便便夸毗子,荣耀更相持。
务光让天下,商贾竞刀锥。
已矣行采芝,万世同一时。
吾爱鬼谷子,青溪无垢氛。
囊括经世道,遗身在白云。
七雄方龙斗,天下久无君。
浮荣不足贵,遵养晦时文。
舒可弥宇宙,卷之不盈分。
岂徒山木寿,空与麋鹿群。
呦呦南山鹿,罹罟以媒和。
招摇青桂树,幽蠹亦成科。
世情甘近习,荣耀纷如何。
怨憎未相复,亲爱生祸罗。
瑶台倾巧笑,玉杯殒双蛾。
谁见枯城蘖,青青成斧柯。
林居病时久,水木澹孤清。
闲卧观物化,悠悠念无生。
青春始萌达。朱火已满盈。
徂落方自此,感叹何时平。
临歧泣世道,天命良悠悠。
昔日殷王子,玉马遂朝周。
宝鼎沦伊谷,瑶台成古丘。
西山伤遗老,东陵有故侯。
贵人难得意,赏爱在须臾。
莫以心如玉,探他明月珠。
昔称夭桃子,今为舂市徒。
鸱鸮悲东国,麋鹿泣姑苏。
谁见鸱夷子,扁舟去五湖。
圣人去已久,公道缅良难。
蚩蚩夸毗子,尧禹以为谩。
骄荣贵工巧。势利迭相干。
燕王尊乐毅,分国愿同欢。
鲁连让齐爵,遗组去邯郸。
伊人信往矣,感激为谁叹。
幽居观天运,悠悠念群生。
终古代兴没,豪圣莫能争。
三季沦周赧,七雄灭秦嬴。
复闻赤精子,提剑入咸京。
炎光既无象,晋虏复纵横。
尧禹道已昧,昏虐势方行。
岂无当世雄,天道与胡兵。
咄咄安可言,时醉而未醒。
仲尼溺东鲁,伯阳遁西溟。
大运自古来,旅人胡叹哉。
逶迤势已久,骨鲠道斯穷。
岂无感激者,时俗颓此风。
灌园何其鄙,皎皎於陵中。
世道不相容,喈喈张长公。
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
黄屋非尧意,瑶台安可论。
吾闻西方化,清净道弥敦。
奈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
云构山林尽,瑶图珠翠烦。
鬼工尚未可,人力安能存。
夸愚适增累,矜智道逾昏。
玄天幽且默,群议曷嗤嗤。
圣人教犹在,世运久陵夷。
一绳将何系,忧醉不能持。
去去行采芝,勿为尘所欺。
蜻蛉游天地,与世本无患。
飞飞未能止,黄雀来相干。
穰侯富秦宠,金石比交欢。
出入咸阳里,诸侯莫敢言。
宁知山东客,激怒秦王肝。
布衣取丞相,千载为辛酸。
微霜知岁晏,斧柯始青青。
况乃金天夕,浩露沾群英。
登山望宇宙,白日已西暝。
云海方荡潏,孤鳞安得宁。
翡翠巢南海,雄雌珠树林。
何知美人意,骄爱比黄金。
杀身炎州里,委羽玉堂阴。
旖旎光首饰,葳蕤烂锦衾。
岂不在遐远,虞罗忽见寻。
多材信为累,叹息此珍禽。
挈瓶者谁子,姣服当青春。
三五明月满,盈盈不自珍。
高堂委金玉,微缕悬千钧。
如何负公鼎,被夺笑时人。
玄蝉号白露,兹岁已蹉跎。
群物从大化,孤英将奈何。
瑶台有青鸟,远食玉山禾。
昆仑见玄凤,岂复虞云罗。
荒哉穆天子,好与白云期。
宫女多怨旷,层城闭蛾眉。
日耽瑶池乐,岂伤桃李时。
青苔空萎绝,白发生罗帷。
朝发宜都渚,浩然思故乡。
故乡不可见,路隔巫山阳。
巫山彩云没,高丘正微茫。
伫立望已久,涕落沾衣裳。
岂兹越乡感,忆昔楚襄王。
朝云无处所,荆国亦沦亡。
昔日章华宴,荆王乐荒淫。
霓旌翠羽盖,射兕云梦林。
朅来高唐观,怅望云阳岑。
雄图今何在,黄雀空哀吟。
丁亥岁云暮,西山事甲兵。
赢粮匝邛道,荷戟争羌城。
严冬阴风劲,穷岫泄云生。
昏曀无昼夜,羽檄复相惊。
拳局竞万仞,崩危走九冥。
籍籍峰壑里,哀哀冰雪行。
圣人御宇宙,闻道泰阶平。
肉食谋何失,藜藿缅纵横。
可怜瑶台树,灼灼佳人姿。
碧华映朱实,攀折青春时。
岂不盛光宠,荣君白玉墀。
但恨红芳歇,凋伤感所思。
朅来豪游子,势利祸之门。
如何兰膏叹,感激自生冤。
众趋明所避,时弃道犹存。
云渊既已失,罗网与谁论。
箕山有高节,湘水有清源。
唯应白鸥鸟,可为洗心言。
索居犹几日,炎夏忽然衰。
阳彩皆阴翳,亲友尽睽违。
登山望不见,涕泣久涟洏。
宿梦感颜色,若与白云期。
马上骄豪子,驱逐正蚩蚩。
蜀山与楚水,携手在何时。
金鼎合神丹,世人将见欺。
飞飞骑羊子,胡乃在峨眉。
变化固幽类,芳菲能几时。
疲疴苦沦世,忧痗日侵淄。
眷然顾幽褐,白云空涕洟。
朔风吹海树,萧条边已秋。
亭上谁家子,哀哀明月楼。
自言幽燕客,结发事远游。
赤丸杀公吏,白刃报私仇。
避仇至海上,被役此边州。
故乡三千里,辽水复悠悠。
每愤胡兵入,常为汉国羞。
何知七十战,白首未封侯。
本为贵公子,平生实爱才。
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
西驰丁零塞,北上单于台。
登山见千里,怀古心悠哉。
谁言未亡祸,磨灭成尘埃。
浩然坐何慕,吾蜀有峨眉。
念与楚狂子,悠悠白云期。
时哉悲不会,涕泣久涟洏。
梦登绥山穴,南采巫山芝。
探元观群化,遗世从云螭。
婉娈时永矣,感悟不见之。
朝入云中郡,北望单于台,
胡秦何密迩,沙朔气雄哉。
藉藉天骄子,猖狂已复来。
塞垣无名将,亭堠空崔嵬。
咄嗟吾何叹,边人涂草莱。
仲尼探元化,幽鸿顺阳和。
大运自盈缩,春秋递来过。
盲飙忽号怒,万物相纷劘。
溟海皆震荡,孤凤其如何。
chén zǐ áng gǎn yù shī sān shí bā shǒu
月牙儿在西海开始生长,隐没的太阳就变化上升。
圆月正向东方运行满盈,阴暗月魄已在早晨凝成。
从混沌元气萌生了天地,三代纪元就已交替废兴。
天道谅必还是这样存在,三正五德谁能加以确证?
兰草杜若生长春夏时节,茎叶茂盛多么美好青葱。
幽雅孤高独擅林中美色,红花覆盖着紫色的株茎。
和煦阳光缓缓走向夜晚,袅袅的秋风已悄悄来临。
一年的繁花都飘摇零落,美好意愿终究如何完成?
苍苍茫茫的丁零族要塞,古往今来道路荒僻遥远。
岗楼哨所多么颓败孤单,暴尸荒野没有完整躯干。
漫天黄沙起于大漠之南,灿烂的太阳隐没在西边。
汉朝排遣了三十万士卒,曾经前来与匈奴族争战。
只见他们纷纷战死沙场,谁来怜悯边疆老幼孤单?
乐羊做了魏国的将军,吞食儿子去追求军功。
亲生骨肉还如此刻薄,对待他人怎么会尽忠?
我听说那个中山国相,便托子给放麂的老翁。
孤苦的小兽不忍加害,更何况侍奉君主后代。
集市商贩自负机巧聪明,对于道术却似无知幼童。
倾轧争夺相互夸耀奢侈,不知自身究竟怎样送终。
难道没有见那得到神仙,观察世道潜身玉壶之中?
深远莫测地抛弃了尘世,顺应造化进入宇宙无穷。
我看那神龙的变化无穷,就知它是最高阳气之精。
岩石成林多么阴暗壅塞,洞穴深邃无法将它挡住。
古时候的得道成仙之路,确是与那造化合而为一。
玄妙感应并非喑昧识见,有谁能够测知其中奥秘?
世上人拘泥于眼见为实,醉醺醺地嘲笑丹经真义。
昆仑山上有那美玉仙树,他们怎能采到它的花蕊?
光明的太阳总不回人间,春天的季节已到了晚暮。
望茫茫天地我想些什么,归隐山林观察宇宙妙道。
万花纷谢在这晦暗时节,杜鹃悲鸣声声摧人耳鼓。
远古的浑朴世风已衰颓,有谁能认识那高士巢父?
我观察混沌时代的变化,太阳月亮沦没黑暗之中。
阴气和阳气互相来结合,天地之间才有万物众生。
孔子推尊的是易经太极,老子贵重的是自然无穷。
西方的佛祖别号金仙子,崇尚的教义是因缘无明。
如果空与色都归于寂灭,那前世因缘又何须完成!
名位礼教确实多而杂乱,人生到死都还争执不停。
圣人从不公开宣讲天命,害怕世人淆乱它的本真。
究竟为什么宫嵩那帮人,用诡诞的谶言贻害世人。
先天的预测诚然很美好,造成国家动乱谁是祸因?
修建长城本为防备胡寇,秦朝的祸殃却发自皇亲。
赤精之谶已迷惑了汉帝,王子年又怎能拯救前秦?
快快离去到那桃李花下,多言而横死者密密麻麻。
隐居不出观察人群动静,人们愤愤地正争夺名利。
彼此谗言诽谤相互侵害,利害攸关纷纷谎言相欺。
夸夸其谈趋炎附势之徒,只为荣耀越发争执对立。
务光辞让掉商汤的天下,行商坐贾竞争刀锥微利。
算了吧还是去采集芝草,千年万代无异短暂一时。
我喜欢那位鬼谷先生,远离尘浊在青溪山居。
掌握所有的经世之道,独住山上与白云相处。
战国七雄正龙争虎斗,天下大乱没有了君主。
浮华虚荣不值得珍惜,怀抱这时代文化不露。
舒展道术可充满宇宙,卷起则不满一分厚度。
哪想如山树无用长寿,空自与野鹿同群为伍。
南山的鹿群呦呦和鸣,落网全因驯鹿来勾引。
招摇山上的青青桂树,蛀虫把树身啃蚀一空。
人情乐意为君主亲幸,荣耀纷纷是何等情景?
怨仇还不曾给予报复,亲爱的人将灾祸滋生。
瑶台在笑嫣之中倒塌,玉杯在娥眉底下破损。
谁见过荒城枯树萌芽,青青枝条被斧子砍伐!
隐居山林苦于时光久滞,林泉清幽寂静心境淡泊。
我闲躺着观察万物变化,无边地漫想宇宙的起源。
春天草木开始萌芽滋长,夏季它们已经丰盈充满。
然而凋落也正从此开始,何时我才能平息这感叹?
面对岔路口为世道哭泣,天命实在深远难以测料。
昨天都还是殷王的子孙,玉马出现就去朝拜周朝。
宝鼎在洢水瀔水里沉沦,东周瑶台成了荒败土堡。
西山有令人哀伤的遗老,东陵侯爵是秦朝的封号。
那些君王很难讨他们欢心,恩赏宠爱也只在片刻工夫。
不要用你高洁如玉的德操,求取他们珍贵的夜光明珠。
当年堪称艳如桃花的女子,如今沦落成舂米场的囚徒。
鸱鸮抒发周公东征的悲伤,伍子胥痛哭麋鹿将游姑苏。
有谁看见越国功臣鸱夷子,驾一叶小舟离国遨游五湖?
圣人离开我们已经很久,公道距今遥远确实困难。
那些浮夸小人纷纷扰扰,连唐尧夏禹都视为欺骗。
骄宠荣耀全凭善于取巧,为了争权夺利交相干犯。
燕昭王尊奉乐毅为上将,分封昌国情愿同乐共欢。
鲁仲连辞让掉齐国爵禄,抛弃官印就离开了邯郸。
他们确实已经成为过去,心中感动激发为谁生叹?
隐居独处观察天命运遇,想着历史长河中的百姓。
自古以来朝代兴衰更迭,豪杰圣贤没人能抗天命。
三代最后沦没于周赧王,七雄则被秦皇嬴政吞并。
又听说赤龙之子汉高祖,举着利剑进入咸阳京城。
汉朝气数已尽国家动乱,晋代北方民族割据纵横。
尧禹之道已经昏暗不明,昏庸残暴正在世上横行。
难道就缺少当代的英雄,只因为天道竟助佑胡兵。
咄咄怪事哪里能说明白,老天醉了似的还没醒转。
孔子终于东归没于鲁国,老子则往西海高蹈遁隐。
天命运遇自古以来如此,孤独之人为何感叹悲鸣?
邪曲之势已经积久,正直之道困顿难行。
难道没有感奋之人,眼下这种风气衰零。
替人灌园多么鄙陋,品质高洁安居於陵。
世道不能容其存身,张长公啊可佩可敬。
圣人从来不自私自利,忧虑黎庶而想要拯济。
坐拥王位不是尧本意,美玉高台哪里可论说!
我听说西方传来佛教,清净的道义越发厚笃。
为什么用尽黄金宝玉,以那奢靡的镌雕为贵?
庙宇高耸山林却伐净,精美宝像过多缀珠翠。
鬼斧神工尚且不能成,人工之力又如何能及?
夸耀愚民恰增添烦累,自负智巧治道更昏聩。
苍苍青天寂静而无声,众说纷纭有多么杂乱!
圣人的教诲仍然存在,世道一直在衰落变迁。
一条绳索能拴住什么,忧心如醉却无法扶持。
走吧走吧去采摘芝草,不要被世俗欺骗污染。
蜻蜓在天地之间游戏,对他物本来没有患害。
飞呵飞呵还没有离开,黄雀便过来干涉侵犯。
魏冉深受秦王的恩宠,君臣交好坚如金石般。
在咸阳城里进进出出,哪个诸侯也不敢进言。
怎知道来个山东说客,一番话激怒秦王肺肝。
一介平民取代了丞相,千年来使人辛酸伤感。
轻霜降下知年节已晚,斧子砍伐那青青枝丫。
何况正是金秋的傍晚,繁露沾润了大地百花。
登上高山放眼望世界,光明的太阳已经西下。
浩渺云海正摇荡汹涌,孤鱼儿想安宁也无法!
翡翠鸟儿筑巢在南海,雌雄伴飞珠玉树林间。
哪里晓得美人的心思,娇贵爱怜像黄金一般。
在炎热南州身遭杀害,羽毛堆积在高堂后面。
翠羽鲜亮使首饰闪光,华丽羽毛令锦被灿烂。
难道不是已躲得很远,突然却被捕猎人寻见。
材美本来是一种牵累,我为这珍禽深深嗟叹。
那个拿壶打水人是谁?明媚春光里身着华服。
好像十五的明月圆满,美好而不知珍惜自保。
高堂上堆积黄金美玉,像细线吊挂千钧铁砣。
为什么那治国的宰相,削职被世人耻笑羞辱?
黑蝉儿在白鹭时节啼鸣,这一年已经白白地过去。
万物随着大自然而变化,孤单的花朵对此能如何?
西王母瑶台有神异青鸟,它远在玉山啄食那木禾。
昆仑山上看见黑色凤凰,难道它还怕穿云的网罗?
多么荒唐啊穆天子,喜同神仙邀约往来。
宫中女子怨恨旷居,深宫高阙关锁粉黛。
日日沉溺瑶池宴乐,哪管宫女伤春情怀。
路上青苔空自枯干,宫闱紧闭宫女头白。
清早离开宜都江边,思绪飞荡想念家园。
故乡可是无法看见,道路阻隔巫山之南。
巫山顶上彩云出没,高丘险阻模糊难辨。
独自站立遥望已久,珠泪滚落沾湿衣衫。
难道只是离乡伤感,原来忆起襄王当年。
神女朝云飘无定所,楚国终也衰亡沦湮。
从前章华台的欢宴,楚王游乐荒淫纵情。
彩色旌旗翠羽帷盖,捕射犀兕云梦之林。
此番来到高唐古观,怅然遥望云阳之岭。
宏图伟略今在哪里?黄雀遭擒徒自悲鸣。
在丁亥这一年岁末,蜀郡西山发生战争。
负粮绕走邛崃山道,扛戟惊动生羌寨城。
严冬山风阴寒强劲,荒僻山谷云雾蒸腾。
天色阴暗不辨昏晓,插羽檄书又传警声。
弓身竞上万仞高峰,山石欲崩地狱深深。
拥挤杂乱穿行峰谷,踩雪踏冰一片哀鸣。
圣人统治天下之世,听说三台星座太平。
执政高官多么失策,百姓憔悴奔走远征。
呵呵那些外出豪游的人,追求势利开启祸患之门。
何必叹息兰膏因材而尽,感动激发自己造成怨愤。
众人所趋指明躲避所在,被时世抛弃而道义尚存。
既然失去了白云和深渊,投入罗网跟谁说理评论?
箕山之下有许由的高节,湘水之中有屈原的清贞。
只应当交游海上白鸥鸟,可对它们倾吐荡涤机心。
玉台之树多可爱,丰茂艳丽似美人。
碧玉花照红果实,攀折要趁春时分。
难道恩宠还不盛,白玉殿前令君荣。
只恨红花终衰败,零落感伤思绪纷。
离群独处只几天,炎炎暑热忽衰竭。
阳光都被乌云掩,亲朋好友全分别。
登上高山看不见,哭泣良久泪不绝。
常常感叹容颜变,才同白云订盟契。
骄横之辈骑马上,追逐名利忙不歇。
蜀国山与楚地水,等到何时手相携?
金色宝鼎炼出灵丹,世上的人将被欺骗。
骑羊如飞那一神仙,为何会在峨眉山巅?
变化必然化为异类,人的年华能有几天?
疲病折磨沉沦时间,忧愁悔恨每噬心田。
深情眷念隐士衣衫,空望白云涕泪满面。
北方吹动渤海边树木,满目萧条边地已深秋。
哨亭上是哪家的子弟,悲声发自月光下岗楼。
自称从幽燕来此异地,束发成人就离家远游。
探得红丸杀过公府官,手执利剑报过私家仇。
躲避仇家来到渤海上,从军服役将边城防守。
故乡遥远在三千里外,辽河水依旧悠悠长流。
每每痛恨契丹兵来犯,常常替中国忍辱蒙羞。
哪知将军身经七十战,直到白头还未曾封侯!
我本是富贵人家子弟,平素确实是赏爱才干。
感慨时势想报效国家,拔剑奋起在草野之间。
向西驰奔到丁零古塞,往北将单于之台登攀。
登山极目见千里辽阔,怀想古昔任思绪悠远。
谁说还没有忘却战祸,历史已磨灭成了灰烟。
思绪飞扬因为爱慕什么?我们蜀中有一座峨眉山。
想与楚国那位狂人交游,期约在那悠悠白云之间。
时世啊不能遇合真悲哀,伤心哭泣很久涕泪满面。
睡梦之中登临绥山洞穴,采摘巫山芝草到了南边。
探索自然观察万物变化,弃俗世随螭龙遨游云间。
神龙飞腾将长久离去了,醒来它的踪影遍寻不见。
清早进入云中古郡,向北瞭望单于之台。
突厥与我挨得多近,漠北称雄气势豪悍。
嘈杂喧嚣天之骄子,已经再次猖狂来犯。
边关要塞缺少名将,亭堡空自高耸云汉。
唉声连连我叹什么?边民横死血染荒原。
孔子探究大自然的变化,北雁南飞顺应阳和规律。
天道运转自然伸缩进退,春与秋的来去先后交迭。
疾劲的暴风忽然间怒号,天地间万物相互受摧折。
浩瀚的大海都波涛震荡,孤高的凤鸟又奈其谁何?
陈子昂《感遇诗三十八首》
1
00:00:00,000 --> 00:00:09,366
陈子昂《感遇诗三十八首》
2
00:00:09,366 --> 00:00:18,466
微月生西海,幽阳始代升。
3
00:00:18,466 --> 00:00:27,733
圆光正东满,阴魄已朝凝。
4
00:00:27,733 --> 00:00:36,733
太极生天地,三元更废兴。
5
00:00:36,733 --> 00:00:46,466
至精谅斯在,三五谁能征。
6
00:00:46,466 --> 00:00:55,133
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
7
00:00:55,133 --> 00:01:04,000
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
8
00:01:04,000 --> 00:01:12,866
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
9
00:01:12,866 --> 00:01:23,733
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
10
00:01:23,733 --> 00:01:32,700
苍苍丁零塞,今古缅荒途。
11
00:01:32,700 --> 00:01:40,333
亭堠何摧兀,暴骨无全躯。
12
00:01:40,333 --> 00:01:48,800
黄沙幕南起,白日隐西隅。
13
00:01:48,800 --> 00:01:56,333
汉甲三十万,曾以事匈奴。
14
00:01:56,333 --> 00:02:06,466
但见沙场死,谁怜塞上孤。
15
00:02:06,466 --> 00:02:14,600
乐羊为魏将,食子殉军功。
16
00:02:14,600 --> 00:02:21,933
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
17
00:02:21,933 --> 00:02:29,266
吾闻中山相,乃属放麑翁。
18
00:02:29,266 --> 00:02:40,066
孤兽犹不忍,况以奉君终。
19
00:02:40,066 --> 00:02:48,233
市人矜巧智,于道若童蒙。
20
00:02:48,233 --> 00:02:56,033
倾夺相夸侈,不知身所终。
21
00:02:56,033 --> 00:03:04,100
曷见玄真子,观世玉壶中。
22
00:03:04,100 --> 00:03:14,600
窅然遗天地,乘化入无穷。
23
00:03:14,600 --> 00:03:23,066
吾观龙变化,乃知至阳精。
24
00:03:23,066 --> 00:03:30,133
石林何冥密,幽洞无留行。
25
00:03:30,133 --> 00:03:37,500
古之得仙道,信与元化并。
26
00:03:37,500 --> 00:03:44,566
玄感非象识,谁能测沈冥。
27
00:03:44,566 --> 00:03:52,700
世人拘目见,酣酒笑丹经。
28
00:03:52,700 --> 00:04:00,033
昆仑有瑶树,安得采其英。
29
00:04:00,033 --> 00:04:08,433
白日每不归,青阳时暮矣。
30
00:04:08,433 --> 00:04:17,533
茫茫吾何思,林卧观无始。
31
00:04:17,533 --> 00:04:26,866
众芳委时晦,鶗鴂鸣悲耳。
32
00:04:26,866 --> 00:04:37,333
鸿荒古已颓,谁识巢居子。
33
00:04:37,333 --> 00:04:46,466
吾观昆仑化,日月沦洞冥。
34
00:04:46,466 --> 00:04:53,900
精魄相交会,天壤以罗生。
35
00:04:53,900 --> 00:05:01,733
仲尼推太极,老聃贵窈冥。
36
00:05:01,733 --> 00:05:09,766
西方金仙子,崇义乃无明。
37
00:05:09,766 --> 00:05:18,333
空色皆寂灭,缘业定何成。
38
00:05:18,333 --> 00:05:29,866
名教信纷藉,死生俱未停。
39
00:05:29,866 --> 00:05:39,033
圣人秘元命,惧世乱其真。
40
00:05:39,033 --> 00:05:48,166
如何嵩公辈,诙谲误时人。
41
00:05:48,166 --> 00:05:55,566
先天诚为美,阶乱祸谁因。
42
00:05:55,566 --> 00:06:02,900
长城备胡寇,嬴祸发其亲。
43
00:06:02,900 --> 00:06:09,533
赤精既迷汉,子年何救秦。
44
00:06:09,533 --> 00:06:20,966
去去桃李花,多言死如麻。
45
00:06:20,966 --> 00:06:28,900
深居观元化,悱然争朵颐。
46
00:06:28,900 --> 00:06:36,700
谗说相啖食,利害纷㘈㘈。
47
00:06:36,700 --> 00:06:45,366
便便夸毗子,荣耀更相持。
48
00:06:45,366 --> 00:06:54,900
务光让天下,商贾竞刀锥。
49
00:06:54,900 --> 00:07:05,900
已矣行采芝,万世同一时。
50
00:07:05,900 --> 00:07:14,300
吾爱鬼谷子,青溪无垢氛。
51
00:07:14,300 --> 00:07:22,400
囊括经世道,遗身在白云。
52
00:07:22,400 --> 00:07:30,133
七雄方龙斗,天下久无君。
53
00:07:30,133 --> 00:07:36,433
浮荣不足贵,遵养晦时文。
54
00:07:36,433 --> 00:07:43,566
舒可弥宇宙,卷之不盈分。
55
00:07:43,566 --> 00:07:54,033
岂徒山木寿,空与麋鹿群。
56
00:07:54,033 --> 00:08:03,333
呦呦南山鹿,罹罟以媒和。
57
00:08:03,333 --> 00:08:11,766
招摇青桂树,幽蠹亦成科。
58
00:08:11,766 --> 00:08:19,366
世情甘近习,荣耀纷如何。
59
00:08:19,366 --> 00:08:28,166
怨憎未相复,亲爱生祸罗。
60
00:08:28,166 --> 00:08:36,866
瑶台倾巧笑,玉杯殒双蛾。
61
00:08:36,866 --> 00:08:48,233
谁见枯城蘖,青青成斧柯。
62
00:08:48,233 --> 00:08:57,666
林居病时久,水木澹孤清。
63
00:08:57,666 --> 00:09:06,933
闲卧观物化,悠悠念无生。
64
00:09:06,933 --> 00:09:10,700
青春始萌达。
65
00:09:10,700 --> 00:09:15,733
朱火已满盈。
66
00:09:15,733 --> 00:09:25,766
徂落方自此,感叹何时平。
67
00:09:25,766 --> 00:09:35,866
临歧泣世道,天命良悠悠。
68
00:09:35,866 --> 00:09:44,866
昔日殷王子,玉马遂朝周。
69
00:09:44,866 --> 00:09:51,266
宝鼎沦伊谷,瑶台成古丘。
70
00:09:51,266 --> 00:10:01,000
西山伤遗老,东陵有故侯。
71
00:10:01,000 --> 00:10:09,333
贵人难得意,赏爱在须臾。
72
00:10:09,333 --> 00:10:17,533
莫以心如玉,探他明月珠。
73
00:10:17,533 --> 00:10:26,633
昔称夭桃子,今为舂市徒。
74
00:10:26,633 --> 00:10:35,400
鸱鸮悲东国,麋鹿泣姑苏。
75
00:10:35,400 --> 00:10:46,300
谁见鸱夷子,扁舟去五湖。
76
00:10:46,300 --> 00:10:56,500
圣人去已久,公道缅良难。
77
00:10:56,500 --> 00:11:05,433
蚩蚩夸毗子,尧禹以为谩。
78
00:11:05,433 --> 00:11:08,733
骄荣贵工巧。
79
00:11:08,733 --> 00:11:13,433
势利迭相干。
80
00:11:13,433 --> 00:11:22,400
燕王尊乐毅,分国愿同欢。
81
00:11:22,400 --> 00:11:31,366
鲁连让齐爵,遗组去邯郸。
82
00:11:31,366 --> 00:11:44,433
伊人信往矣,感激为谁叹。
83
00:11:44,433 --> 00:11:54,700
幽居观天运,悠悠念群生。
84
00:11:54,700 --> 00:12:04,266
终古代兴没,豪圣莫能争。
85
00:12:04,266 --> 00:12:13,733
三季沦周赧,七雄灭秦嬴。
86
00:12:13,733 --> 00:12:22,500
复闻赤精子,提剑入咸京。
87
00:12:22,500 --> 00:12:30,233
炎光既无象,晋虏复纵横。
88
00:12:30,233 --> 00:12:37,500
尧禹道已昧,昏虐势方行。
89
00:12:37,500 --> 00:12:44,666
岂无当世雄,天道与胡兵。
90
00:12:44,666 --> 00:12:51,300
咄咄安可言,时醉而未醒。
91
00:12:51,300 --> 00:12:59,700
仲尼溺东鲁,伯阳遁西溟。
92
00:12:59,700 --> 00:13:12,366
大运自古来,旅人胡叹哉。
93
00:13:12,366 --> 00:13:20,800
逶迤势已久,骨鲠道斯穷。
94
00:13:20,800 --> 00:13:29,866
岂无感激者,时俗颓此风。
95
00:13:29,866 --> 00:13:39,500
灌园何其鄙,皎皎於陵中。
96
00:13:39,500 --> 00:13:50,866
世道不相容,喈喈张长公。
97
00:13:50,866 --> 00:13:59,366
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
98
00:13:59,366 --> 00:14:08,233
黄屋非尧意,瑶台安可论。
99
00:14:08,233 --> 00:14:16,333
吾闻西方化,清净道弥敦。
100
00:14:16,333 --> 00:14:25,466
奈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
101
00:14:25,466 --> 00:14:32,766
云构山林尽,瑶图珠翠烦。
102
00:14:32,766 --> 00:14:39,800
鬼工尚未可,人力安能存。
103
00:14:39,800 --> 00:14:49,366
夸愚适增累,矜智道逾昏。
104
00:14:49,366 --> 00:14:58,600
玄天幽且默,群议曷嗤嗤。
105
00:14:58,600 --> 00:15:07,200
圣人教犹在,世运久陵夷。
106
00:15:07,200 --> 00:15:15,500
一绳将何系,忧醉不能持。
107
00:15:15,500 --> 00:15:26,000
去去行采芝,勿为尘所欺。
108
00:15:26,000 --> 00:15:34,833
蜻蛉游天地,与世本无患。
109
00:15:34,833 --> 00:15:45,500
飞飞未能止,黄雀来相干。
110
00:15:45,500 --> 00:15:53,500
穰侯富秦宠,金石比交欢。
111
00:15:53,500 --> 00:16:00,700
出入咸阳里,诸侯莫敢言。
112
00:16:00,700 --> 00:16:08,300
宁知山东客,激怒秦王肝。
113
00:16:08,300 --> 00:16:18,300
布衣取丞相,千载为辛酸。
114
00:16:18,300 --> 00:16:27,066
微霜知岁晏,斧柯始青青。
115
00:16:27,066 --> 00:16:34,200
况乃金天夕,浩露沾群英。
116
00:16:34,200 --> 00:16:42,266
登山望宇宙,白日已西暝。
117
00:16:42,266 --> 00:16:52,433
云海方荡潏,孤鳞安得宁。
118
00:16:52,433 --> 00:17:00,700
翡翠巢南海,雄雌珠树林。
119
00:17:00,700 --> 00:17:09,333
何知美人意,骄爱比黄金。
120
00:17:09,333 --> 00:17:18,566
杀身炎州里,委羽玉堂阴。
121
00:17:18,566 --> 00:17:25,833
旖旎光首饰,葳蕤烂锦衾。
122
00:17:25,833 --> 00:17:34,966
岂不在遐远,虞罗忽见寻。
123
00:17:34,966 --> 00:17:45,233
多材信为累,叹息此珍禽。
124
00:17:45,233 --> 00:17:52,566
挈瓶者谁子,姣服当青春。
125
00:17:52,566 --> 00:18:00,566
三五明月满,盈盈不自珍。
126
00:18:00,566 --> 00:18:09,466
高堂委金玉,微缕悬千钧。
127
00:18:09,466 --> 00:18:19,166
如何负公鼎,被夺笑时人。
128
00:18:19,166 --> 00:18:28,033
玄蝉号白露,兹岁已蹉跎。
129
00:18:28,033 --> 00:18:36,000
群物从大化,孤英将奈何。
130
00:18:36,000 --> 00:18:44,600
瑶台有青鸟,远食玉山禾。
131
00:18:44,600 --> 00:18:52,033
昆仑见玄凤,岂复虞云罗。
132
00:18:52,033 --> 00:19:00,466
荒哉穆天子,好与白云期。
133
00:19:00,466 --> 00:19:09,300
宫女多怨旷,层城闭蛾眉。
134
00:19:09,300 --> 00:19:17,866
日耽瑶池乐,岂伤桃李时。
135
00:19:17,866 --> 00:19:26,133
青苔空萎绝,白发生罗帷。
136
00:19:26,133 --> 00:19:36,100
朝发宜都渚,浩然思故乡。
137
00:19:36,100 --> 00:19:46,233
故乡不可见,路隔巫山阳。
138
00:19:46,233 --> 00:19:57,066
巫山彩云没,高丘正微茫。
139
00:19:57,066 --> 00:20:08,666
伫立望已久,涕落沾衣裳。
140
00:20:08,666 --> 00:20:18,733
岂兹越乡感,忆昔楚襄王。
141
00:20:18,733 --> 00:20:31,666
朝云无处所,荆国亦沦亡。
142
00:20:31,666 --> 00:20:41,033
昔日章华宴,荆王乐荒淫。
143
00:20:41,033 --> 00:20:48,366
霓旌翠羽盖,射兕云梦林。
144
00:20:48,366 --> 00:20:56,733
朅来高唐观,怅望云阳岑。
145
00:20:56,733 --> 00:21:05,966
雄图今何在,黄雀空哀吟。
146
00:21:05,966 --> 00:21:14,266
丁亥岁云暮,西山事甲兵。
147
00:21:14,266 --> 00:21:22,833
赢粮匝邛道,荷戟争羌城。
148
00:21:22,833 --> 00:21:31,800
严冬阴风劲,穷岫泄云生。
149
00:21:31,800 --> 00:21:41,400
昏曀无昼夜,羽檄复相惊。
150
00:21:41,400 --> 00:21:52,866
拳局竞万仞,崩危走九冥。
151
00:21:52,866 --> 00:22:02,366
籍籍峰壑里,哀哀冰雪行。
152
00:22:02,366 --> 00:22:11,966
圣人御宇宙,闻道泰阶平。
153
00:22:11,966 --> 00:22:24,233
肉食谋何失,藜藿缅纵横。
154
00:22:24,233 --> 00:22:32,833
可怜瑶台树,灼灼佳人姿。
155
00:22:32,833 --> 00:22:41,200
碧华映朱实,攀折青春时。
156
00:22:41,200 --> 00:22:49,733
岂不盛光宠,荣君白玉墀。
157
00:22:49,733 --> 00:22:59,300
但恨红芳歇,凋伤感所思。
158
00:22:59,300 --> 00:23:07,466
朅来豪游子,势利祸之门。
159
00:23:07,466 --> 00:23:17,433
如何兰膏叹,感激自生冤。
160
00:23:17,433 --> 00:23:26,866
众趋明所避,时弃道犹存。
161
00:23:26,866 --> 00:23:36,700
云渊既已失,罗网与谁论。
162
00:23:36,700 --> 00:23:45,466
箕山有高节,湘水有清源。
163
00:23:45,466 --> 00:23:56,733
唯应白鸥鸟,可为洗心言。
164
00:23:56,733 --> 00:24:04,966
索居犹几日,炎夏忽然衰。
165
00:24:04,966 --> 00:24:14,800
阳彩皆阴翳,亲友尽睽违。
166
00:24:14,800 --> 00:24:24,766
登山望不见,涕泣久涟洏。
167
00:24:24,766 --> 00:24:35,533
宿梦感颜色,若与白云期。
168
00:24:35,533 --> 00:24:44,666
马上骄豪子,驱逐正蚩蚩。
169
00:24:44,666 --> 00:24:55,266
蜀山与楚水,携手在何时。
170
00:24:55,266 --> 00:25:04,366
金鼎合神丹,世人将见欺。
171
00:25:04,366 --> 00:25:12,500
飞飞骑羊子,胡乃在峨眉。
172
00:25:12,500 --> 00:25:22,133
变化固幽类,芳菲能几时。
173
00:25:22,133 --> 00:25:30,766
疲疴苦沦世,忧痗日侵淄。
174
00:25:30,766 --> 00:25:42,433
眷然顾幽褐,白云空涕洟。
175
00:25:42,433 --> 00:25:53,100
朔风吹海树,萧条边已秋。
176
00:25:53,100 --> 00:26:03,833
亭上谁家子,哀哀明月楼。
177
00:26:03,833 --> 00:26:13,733
自言幽燕客,结发事远游。
178
00:26:13,733 --> 00:26:22,300
赤丸杀公吏,白刃报私仇。
179
00:26:22,300 --> 00:26:29,866
避仇至海上,被役此边州。
180
00:26:29,866 --> 00:26:38,200
故乡三千里,辽水复悠悠。
181
00:26:38,200 --> 00:26:47,733
每愤胡兵入,常为汉国羞。
182
00:26:47,733 --> 00:27:00,533
何知七十战,白首未封侯。
183
00:27:00,533 --> 00:27:09,433
本为贵公子,平生实爱才。
184
00:27:09,433 --> 00:27:17,033
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
185
00:27:17,033 --> 00:27:25,033
西驰丁零塞,北上单于台。
186
00:27:25,033 --> 00:27:34,600
登山见千里,怀古心悠哉。
187
00:27:34,600 --> 00:27:47,133
谁言未亡祸,磨灭成尘埃。
188
00:27:47,133 --> 00:27:56,666
浩然坐何慕,吾蜀有峨眉。
189
00:27:56,666 --> 00:28:06,433
念与楚狂子,悠悠白云期。
190
00:28:06,433 --> 00:28:16,300
时哉悲不会,涕泣久涟洏。
191
00:28:16,300 --> 00:28:25,500
梦登绥山穴,南采巫山芝。
192
00:28:25,500 --> 00:28:35,233
探元观群化,遗世从云螭。
193
00:28:35,233 --> 00:28:46,866
婉娈时永矣,感悟不见之。
194
00:28:46,866 --> 00:28:56,233
朝入云中郡,北望单于台,
195
00:28:56,233 --> 00:29:06,200
胡秦何密迩,沙朔气雄哉。
196
00:29:06,200 --> 00:29:14,366
藉藉天骄子,猖狂已复来。
197
00:29:14,366 --> 00:29:24,500
塞垣无名将,亭堠空崔嵬。
198
00:29:24,500 --> 00:29:34,400
咄嗟吾何叹,边人涂草莱。
199
00:29:34,400 --> 00:29:42,400
仲尼探元化,幽鸿顺阳和。
200
00:29:42,400 --> 00:29:51,400
大运自盈缩,春秋递来过。
201
00:29:51,400 --> 00:30:00,600
盲飙忽号怒,万物相纷劘。
202
00:30:00,600 --> 00:30:09,433
溟海皆震荡,孤凤其如何。
唐代
táng dà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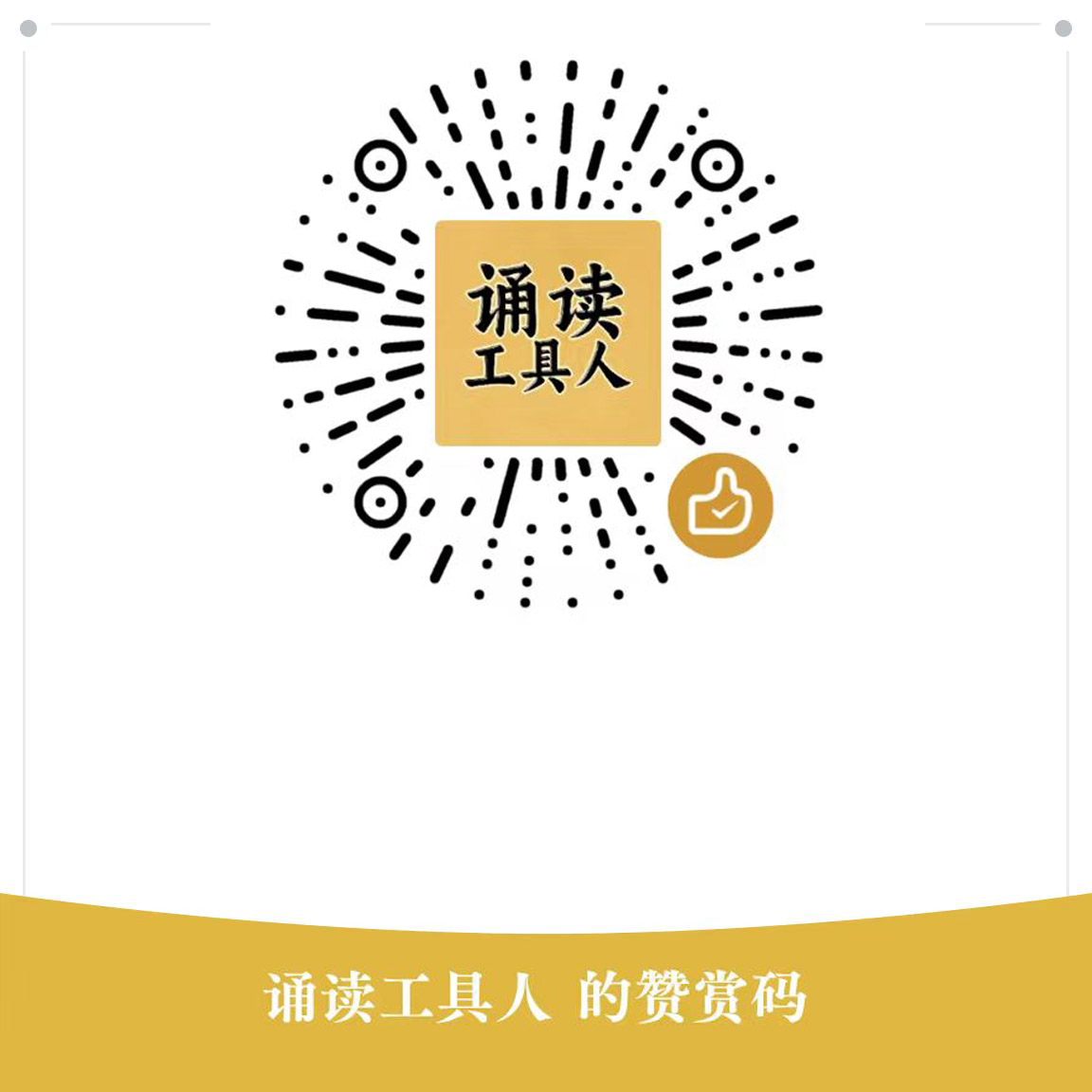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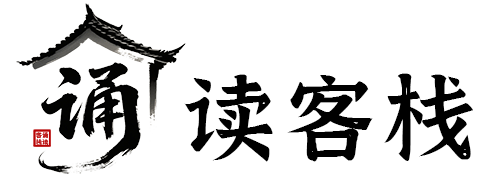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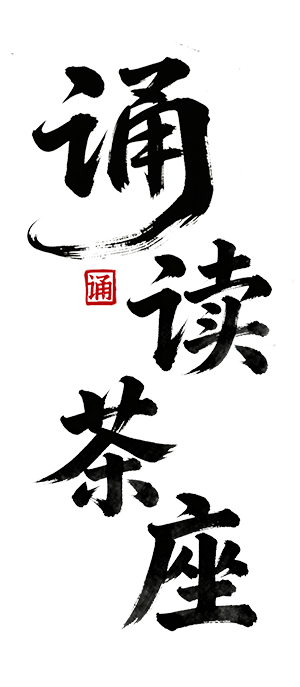
 0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