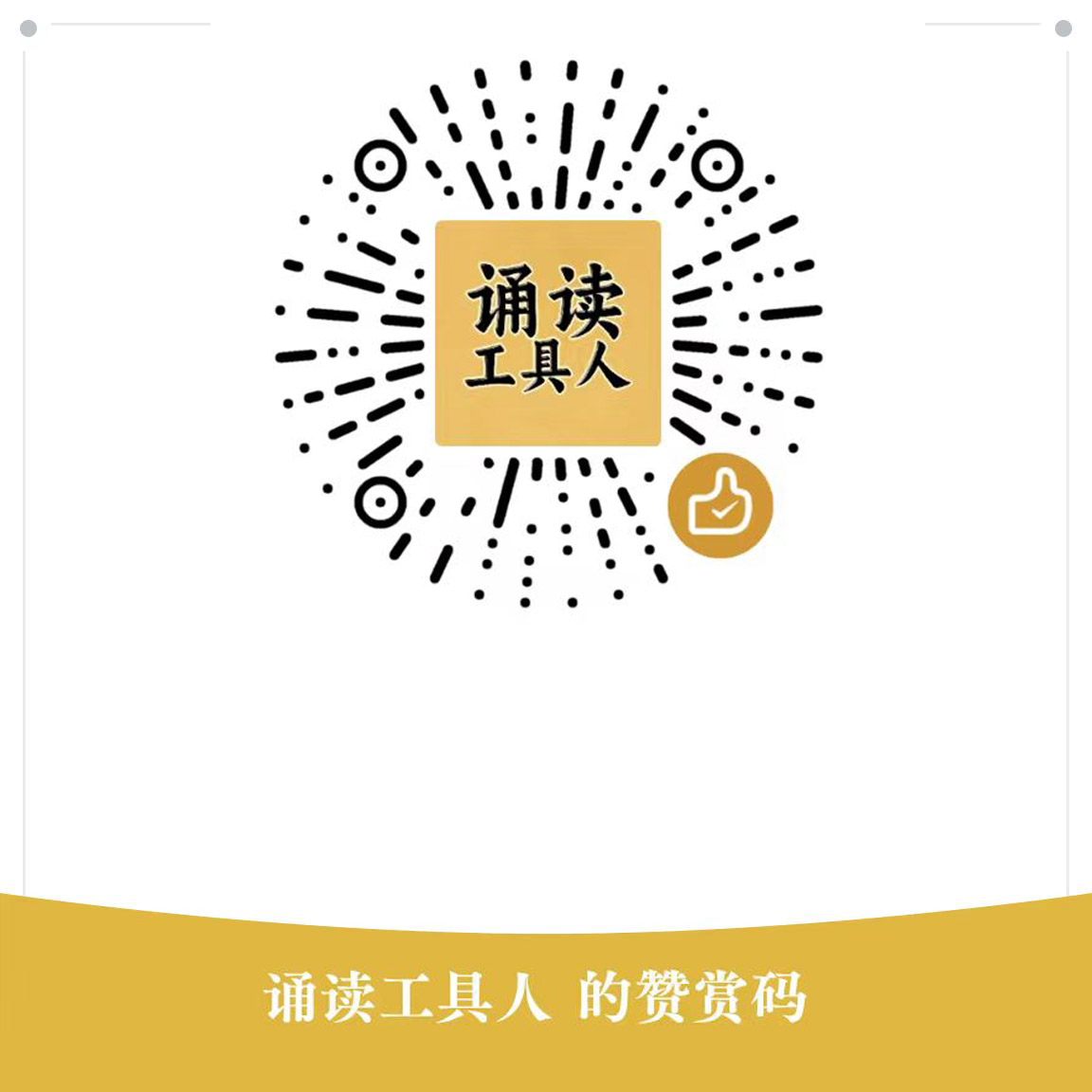小
中
大
录制于:2025年7月20日

仅永久VIP可访问

 0
22
0
0
22
0


确定要删除这条记录吗?此操作不可恢复。
编辑于:2025-08-02 15:17:14
杂曲歌辞·长干曲四首
拼音译文音对译
正文字数:80
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
停舟暂借问,或恐是同乡。
家临九江水,去来九江侧。
同是长干人,生小不相识。
下渚多风浪,莲舟渐觉稀。
那能不相待,独自逆潮归。
三江潮水急,五湖风浪涌。
由来花性轻,莫畏莲舟重。
jūn jiā hé chù zhù qiè zhù zài héng táng
tíng zhōu zàn jiè wèn huò kǒng shì tóng xiāng
jiā lín jiǔ jiāng shuǐ qù lái jiǔ jiāng cè
tóng shì cháng gān rén shēng xiǎo bù xiāng shí
xià zhǔ duō fēng làng lián zhōu jiàn jué xī
nǎ néng bù xiāng dài dú zì nì cháo guī
sān jiāng cháo shuǐ jí wǔ hú fēng làng yǒng
yóu lái huā xìng qīng mò wèi lián zhōu zhòng
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
你家住在什么地方,我家住在横塘一带。
停舟暂借问,或恐是同乡。
家临九江水,去来九江侧。
同是长干人,生小不相识。
下渚多风浪,莲舟渐觉稀。
那能不相待,独自逆潮归。
三江潮水急,五湖风浪涌。
由来花性轻,莫畏莲舟重。
cuī hào zá qǔ gē cí · cháng gān qǔ sì shǒu
你家住在什么地方,我家住在横塘一带。
停船我来打听一下,或许我们还是同乡。
我家就临靠着九江,来去都在九江边上。
我们同是长干的人,可我们从小不相识。
下渚的风浪很多,采莲的船只渐渐少了。
哪能不相等待,自己独自迎着潮水归去呢?
三江五湖潮水很急,江湖上风浪常起。
女子轻如花朵,不要怕莲舟过重而不能弄潮。
崔颢《杂曲歌辞·长干曲四首》
1
00:00:00,000 --> 00:00:11,400
崔颢《杂曲歌辞·长干曲四首》
2
00:00:11,400 --> 00:00:20,333
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
3
00:00:20,333 --> 00:00:29,900
停舟暂借问,或恐是同乡。
4
00:00:29,900 --> 00:00:37,500
家临九江水,去来九江侧。
5
00:00:37,500 --> 00:00:46,866
同是长干人,生小不相识。
6
00:00:46,866 --> 00:00:55,533
下渚多风浪,莲舟渐觉稀。
7
00:00:55,533 --> 00:01:05,466
那能不相待,独自逆潮归。
8
00:01:05,466 --> 00:01:13,333
三江潮水急,五湖风浪涌。
9
00:01:13,333 --> 00:01:21,200
由来花性轻,莫畏莲舟重。
唐代
táng dài